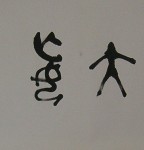作者蕭功秦按語: 《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發表了李維民先生“清末新政'破產'的教訓”一文,對拙文“從清末改革想到當代革命”(今年第四期)提出批評商榷。李先生認為清末改革的失敗原因,並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機沉重壓力下,清王朝無力駕馭大幅度的急劇變革”,而是因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 ”恰好有關清末改革的拙著《危機中的變革》一書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現將我為該書寫的“再版序”在這裡發表,以作為對李維民先生批評的回應。相信這場一百年前的充滿矛盾與困境的、複雜而豐富的改革運動,會引起當代國人濃厚的興趣。
這本《危機中的變革》是考察晚清帝國改革運動如何走向失敗的歷史著作,它出版於十年以前,本書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前夕有幸再次出版,分享著百年祭的厚重歷史感。作者很希望這本書能為理解百年前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那場新政改革,以及由此引發的辛亥革命的背景,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從世界歷史來看,為什麼有的改革能消弭革命,有的改革卻會成為革命的催化劑?這也是本書作者所關注的問題。
這本書中試圖回答兩個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命運密切相關的問題。一個是,帝制中國為什麼總是在陷入重大的危機以後,才得以過遲地進入了變革的時代?另一個是,危機時代的變革,會陷入什麼矛盾與困境?
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香港學術界,在論述清王朝變革失敗的問題上,以往占主流的觀點是這樣的:保守的清王朝統治者鎮壓了戊戌變法之後,中國又遭受了八國聯軍入侵的災難,然而,此後的清末統治者卻並沒有改革的誠意,在巨大危機壓力下,才不得不進行虛假的新政。日俄戰爭中,由於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制的俄國,統治者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實行預備立憲。由於清王朝統治者對權力的壟斷使國人失望,於是立憲派發動四次請願運動,統治者仍然無動於衷,此外,清廷還將民營股份公司收為國有,破壞了人民應享有的築路權,於是,人民為了保衛自己的產權不受掠奪而奮起抗爭,發起保路運動,並最終轉向排滿革命。在以往的主流敘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場假改革。
然而,我的觀點,正好與這種主流觀點相對立。多年以來,根據我對清末變革史的研究,事實上,戊戌變法是一場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與一批同樣缺乏官場政治經驗的、充滿書生激情的少壯變法人士相結合而發動的不成熟的激進改革。嚴復在對變法運動失敗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時,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書生誤國,庸醫殺人”。可以認為,導致變革悲劇的激進主義,恰恰可以解釋為保守的積重難返的官僚體制的因果報應。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動,並由此引發庚子事變的奇恥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變後事實上也確實成為清末新政的最積極推動者,說她沒有改革誠意實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後幾乎喪失了原來的固執與自信,經常以淚洗臉,她在召見張謇入對,張謇問她“改革是真還是假”,她回答說,“因不好才改良,改革還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說?”當張謇談及改革中的腐敗與人心散亂時,她也百感交集隨之而哭。平心而論,她對新政的期待與改革真誠,是出自於對滿族王朝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危機的揮之不去的憂慮。
應該說,晚清新政也確實有著重要成就。新政已經有了明確的現代化導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項現代化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長達十一年的清末新政給中國帶來的實質性的深刻變化,比起出師未捷的百日維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一位1906年訪問中國的日本學者就曾對北京市容日新月異的變化發出“即將超過東京”的驚嘆。丁韙良、李提摩泰對新政的由衷讚美與樂觀,固然會使我們後人覺得有點幼稚膚淺,然而,正是從這些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的外國人眼中,新政時的中國變化之大,與它僵化不變的過去相比,確實足以令他們欣喜了。
新政早期階段可以稱之為開明專制主義時期,雖然它對社會的動員能力較弱,但卻保持著王朝權力對改革進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的第二階段,中國人對日本立憲的誤讀,對清廷構成一種強大壓力,造成了從開明專制的集權模式向激進的立憲分權模式的急劇轉變。雖然,從長遠來說,中國現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現代化改革初期,這一分權立憲轉變恰恰是這場變革失敗的重要原因。這是因為,對帝制不滿的人們,從此可以藉助於資政院與諮議局的平台,持續地發起激進的速開國會運動,衝擊著政府所剩無幾的統治權威。預備立憲不但沒有增加統治者希望的中國人的政治共識,反而強化了統治者與受治者之間的認同分裂,它實際上起到的作用不僅僅是揚湯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運動發生在距今正好一百週年。事實上,如果不帶有偏見,必須承認,後發展國家修建鐵路,商辦鐵路政策是很難成功的,清廷的鐵路築路權收歸國有政策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合理經濟政策,盛宣懷與四國銀行簽訂的鐵路貸款,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條件的優惠低息的商業貸款,並非什麼賣國條約,然而,由於排滿民族主義的衝擊,使這一原本合理的現代化鐵路政策卻被解釋為賣國之舉,並“歪打正著”地成為一場不成熟的革命的導線。
如果說,以往的主流話語從反滿民族主義或階級鬥爭範式來看待變法與新政,那麼,本書的側重點,則是對傳統官僚帝國面對變革中矛盾的應對之道的冷峻審視,這一視角無疑會對於正在進行新的變革的二十一世紀的改革者,提供更直接的啟示。
二
人們發現,一般而言,一個專制集權的帝國通過改革而走向現代化成功的概率並不很高,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沙皇俄國,以及大清帝國,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戰與民族危機的重重壓力之後,先後陷入改革的泥潭無以自拔,並被改革引發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傳統國家中,只有日本的變革似乎是一個特例。日本的明治維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戰爭中輕而易舉地打敗中國之後,成功地走向現代化。然而,從結構上來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於日本並不是傳統意義的中央集權的帝國,傳統日本是由二百多個獨立自治的藩國構成的、類似於西周分封制的國家。
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集權帝國從改革走向革命的極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麼?傳統國家的集權體制與分散的多元模式,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區別?我發現清末的改革失敗並引發清王朝的崩潰,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劇在於,當統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較充足的權威資源時,統治階層總是缺乏改革的意願;當帝國被列強打敗並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時,例如,當清帝國統治者在甲午戰爭與庚子事變如此嚴重的危機之後,才會在焦慮感的壓力下,進行“狗急跳牆”式的變革。然而,此時的王朝統治者或者由於缺乏審時度勢的改革人材,或者由於戰爭失敗後的民族危機加深,而喪失了統治所必需的權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機狀態下進入改革,那麼,這樣的改革往往缺乏號召力,並會成為革命的催化劑。由於帝國統治者缺乏最起碼的權威資源來對時局進行調控與整合,只會陷入進一步的混亂與危機,於是一切已經為時己晚。
其次,帝國改革之所以困難,還在於人才缺乏,在專制危機條件下的改革,遠比承平時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領袖,更需要一個能闊視遠想的強勢人物來引導國家渡過風險,並把國家引向有希望的未來。這樣的政治家應該具有足夠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與國際經驗。然而,舊帝國官僚體制習於所安的保守性,似乎總是對這樣的人才,起著逆向淘洗的作用。在危機到來以前,以“承龔舊章”為主旨的帝國體制,早已經把此類人士當作異己者過濾一空了。能在這種體制下生存下來並游刃有餘的,恰恰是平庸之輩。當統治者把目光轉向體制外的民間知識分子並讓他們擔當改革大任時,此類人卻沒有最起碼的官僚體制內的政治經驗,這構成專制集權帝制改革的另一個兩難命題。
從中國清末的政治格局來看,當中國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統治者時,無論是光緒皇帝,康梁變法人士,還是庚子事變後頗有真誠改革意願的慈禧太后,或兩宮駕崩後執掌王朝大權的攝政王載灃,都根本無力承擔危難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說中國無法應運而生伊藤博文那樣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於第四次垂簾聽政的權欲,居然讓明知無能的載灃執掌大權,這位攝政王不但判斷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識貧乏,智力平庸,而且還出生於一個神經很脆弱的家族。根據這個家族後人寫的回憶錄記載,這位攝政王一緊張起來就會口吃。當慈禧太后突然撤手人寰時,帝國的命運就已經可想而知了。
第三,清王朝的改革戰略選擇確實存在著重大失誤,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1905年以前的集權的開明專制模式更為合適,而在日俄戰爭刺激下而進行的預備立憲,恰恰是當時主流士大夫官紳的一種觀念誤讀後的政治選擇。而這種分權立憲在政治認同已經發生危機的情況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預備立憲導致大眾的政治參與慾望突然膨脹起來並得以合法地與清政權分庭抗禮,而脆弱的清政府對此已經無力控制。眾所周知,西方國家的君權政治到民主政治的發育,是在社會共識逐漸擴大的情況下分階段擴大的,而中國改革中的政治參與擴大,則是在民族危機與社會不滿日益強烈的壓力下,被迫地擴大的。而危機壓力又恰恰造成社會認同日益分裂,擴大政治參與不但不能達到消解社會不滿的功效,反而會對這種不滿起放大與傳染效應。擴大了的政治參與渠道卻成為社會不滿者攻擊執政者的合法場所。危機中的統治者對此幾無招架之力。
當然,清朝崩亡決不是清朝統治者腐敗無能這一點所能解釋的,它是特殊條件下的多種因素相互影響而發生的:統治者合法性危機下進行的現代化挫折,改革綜合症引起的社會不滿,傳媒的急劇發展引起的傳感效應,在關鍵時期統治者新舊交替出現的治理能力整體水平低下,滿漢矛盾與排滿民族主義在軍人中的傳染等等,所有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來傳播革命種子。
從宏觀的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為什麼大多數集權官僚的專制體制一旦進入改革,反而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陷入進退兩難,並難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運?
概括地說,一元化的專制體制比起日本多元體制來說,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機,其內部大一統的結構,往往缺乏對應危機的多元調適能力。真正能實現穩定變革的社會,其內部需要一種“多元整合機制”。即一個社會內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社會的整合。更具體說,對變化的環境的有效適應,除了政權力量或國家管控與乾預力量之外,還應有地方,個人、社會倫理、意識形態創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間社會組織、以及社會流動方式等等,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會領域的多元因素,均在無形之中有助於實現社會的整合,它們的存在,極大地減輕了中央國家對社會進行全面整合的難度。它們在支持、協助國家實現從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方面,功不可沒。
人們可以發現,在明治轉型期的日本,日本社會就是由許多小規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細胞構成的大共同體,上述多元整合機制,是具有自治傳統的日本藩封體制先天所具備的。當中國的科舉制持續壓抑著創新人材,使中國缺乏足夠應對新環境挑戰的社會精英時,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統體制約束的武士階層中,卻能層出不窮地湧現出現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對日本現代化做出重大貢獻的企業家、海運王、留學生、政治家與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彌太郎、板恆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於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這種多元體制培育了明治維新的中堅力量。他們轉化為現代化的精英。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實現,是因為地方與民間個人具有多元的微觀試錯的機會。地方,民間社會與個人,在國家之外,自主地面對著環境壓力,不斷地進行著微觀的調適,國家作為引洪主渠之外,社會中的多元個體,則發揮著毛細管般的涓涓細流的作用。而這種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專制社會內部先天缺乏的。如果說,日本至少有二百多個藩國與無數的武士這樣的自主細胞,作為試錯主體, 那麼,不幸的是,清代的專制中國,慈禧太后則成為全國唯一的試錯主體,她的權欲使她對清王朝的崩潰要負最大的責任。洋務運動的若干現代化成果之所以獲得,只不過是從湘軍精英轉化過來的沿江沿海封疆大吏們,運用了從大一統專制集權體制中截留下來的可憐的一點自主權而己。中日整合機制之區別,中日改革命運之不同,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於是,缺乏“多元整合機制”的中國就陷入瞭如下惡性循環:危機促成了遲來的改革,遲來的改革又在危機壓力下越來越加大幅度,從而又進一步又導向更深重的危機。轉型期社會矛盾比改革以前還要多並還不斷累積,社會失序就會在人們心目中產生不滿,隨著各種矛盾的“發酵”,這時,“革命”便成為許多人的一種“心理訴求”。在中國,既然滿族統治者是以少數族統治多數族,這種不滿就會被順理成章地解釋為“滿人的惡”,要清除這種惡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
到這時,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就會陷入所謂的“沙堆效應”:那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於高高的沙堆上,就會使龐大無比的沙堆在連鎖的滑坡反應中突然崩陷。
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烏合之眾的、無組織、無領袖、無準備、一盤散沙式的各省新軍一旦起義,就會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發生革命,處於充滿仇視的漢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滿族人,如同處於孤島般充滿恐懼,因為舊勢力自信心太弱,幾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況下就自我解體。例如,辛亥起義規模僅次於湖北的雲南省,全省新軍起義勝利時,因革命而戰死者只不過一百多人。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個國家統治者如此弱不禁風,再也沒有一場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樣,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滿地的爛桃子一樣輕而易舉。與其說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說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敗,是以排滿革命的方式作為表現形式的。
歷史的弔詭並沒有結束,遲來的專制改革必將導致同樣不成熟的革命。雖然在後世看來,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偉大歷史意義,但革命“一不留神”而成功,而“烏合之眾”般的無組織的辛亥革命者,注定無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於是不得不讓權於自己的政治對手袁世凱,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國從此陷入持續數十年的“弱國家”狀態。事實上,二十世紀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更為多災多難時代的開始。此後的民國內閣危機、二次革命與內爭,軍閥割據與統一國家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從晚清帝國改革失敗中得到解釋。
百年以後的今天,專制帝國改革之所以比多元傳統國家改革更難以成功的原因,可以這樣認為,在中國大清王朝體制下,中央王朝國家是唯一試錯主體,而且,王朝國家受儒家官學意識形態教義束縛更大,人們更難從這一教義中擺脫出來。受官學化的儒家正統觀念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們人數眾多,卻只會按一種方式思維,非如此他們一天也無法生活於官僚群體之中,其中很難產生改革所需要的富於創新精神的人才。
此外,中國的大一統官僚體制又對全國進行著有嚴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權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視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間的反應。民間與地方的自主能力無法在體制內發育出來,專制帝國的意識形態可以有效地、強有力地抑制著社會的自主試錯與創新,王朝體制拒絕任何微觀領域的試錯,這就形成強烈的路徑鎖定狀態。任何溫和的創新與變革嘗試都會被壓抑在萌芽狀態,當問題越來越嚴重,百姓越來越不滿,統治者再想進行真誠的改革時,一切已經為時太晚,而受治者們則認定,只有根本摧毀舊體制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更為不幸的是,而這樣的革命本身又會帶來另一種悲劇,即弱勢國家的悲劇。一場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敗,以及革命的兩難,對於豐富改革政治學的歷史經驗資源,應該說也有啟示意義。我們今天的讀者,也會從中獲得智慧與教益。
三
幾年前,記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給我的信中寫道,“歷史提供給我們的,不僅是事實,也不僅是知識,而是要培育我們一種知人論世的能力。我終於了解到歷史是訓練、培育我們思維的一種最重要方式。”
善哉斯言,歷史就是要培養我們“知人論世”的能力,這句話道出了歷史學生命力所在, 我想,這也應該新政治史的目標與努力的方向。
清末變革以悲劇告終,並且是二十世紀更大悲劇的起點,只有悲劇時代的人們,才能對人生與社會產生刻骨銘心的體驗,這是那些幸福而質樸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貴精神資源。只有民族的苦難,才能成為史家研究人性與歷史的最好的原材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時代不幸才會造就深刻的史學家與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二十世紀歷史的開端,以後有更多的悲喜劇等候著史家去發現其意義,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時代不幸史家幸,請記住,我們民族就生活在歷史的富礦脈帶上。
| < 前一個 | 下一個 > |
|---|
- 2011-07-05 - 經歷,卻不能感受: 中國教育如何扼殺學生的創造力?
- 2011-07-02 - 敦煌:水中誕生的沙漠
- 2011-07-02 - 誤解?漢字在日中交流中的作用
- 2011-06-12 - 優雅的筆觸:淺談中國國畫藝術
- 2011-05-15 - 泰戈爾對話愛因斯坦:真理是真實的嗎?那美呢?
- 2011-05-06 - 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題材與文人心態
- 2011-01-23 - 坦然面對死亡 - 大同歷史名人李少蘭
- 2010-10-09 - 光明日報:東西美學的邂逅——中美學者對話身體美學
- 2010-09-16 - 大自然之歌
- 2010-08-19 - 大歷史觀宗師 黃仁宇先生 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