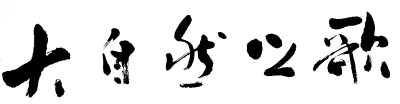陳世旭,著名作家。漢族。 1948年生於南昌市。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江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先後出版長篇小說《將軍鎮》、《世紀神話》等多部,以及《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陳世旭卷》等散文隨筆集、中短篇小說集多部。小說《小鎮上的將軍》、《驚濤》、《馬車》、《鎮長之死》分獲1979年、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7—1988年全國優秀小說獎;首屆魯迅文學獎。
很久了,我們的眼睛只能看見水泥的森林、鋼筋的湖泊和塑料的草原,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很久了,因為已經適應了人工的世界,人類的退化成為一件更為可悲的事情——我們已經忘記了大自然的存在,聽不到流雲的歡歌,看不到藍天的舞蹈,聞不到大地的芳香,再沒有福氣享受生命的狂歡!
很久了,虛擬的電子網絡複製著我們虛幻的快樂,真實離我們遠去,真切離我們遠去,真知亦會隨之離我們遠去嗎?
為了尋回人生的真諦,讓我們隨同著名作家陳世旭,踏上這次回歸大自然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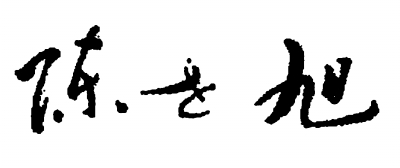
森林
在整個世界,除了水,我最喜歡的就是森林。
繁衍自強的森林是生之意趣。森林收容了一幕又一幕悲喜劇。
瀰漫在森林間的沉寂與神秘,為藝術提供了深沉、寧靜的心理背景。多少個世紀以來,森林始終滋潤著人們的鄉愁與詩心。這就是為什麼索爾·貝婁會說:“藝術從森林開始。”
森林多麼好。森林有花有草,森林有云有霧,森林有風有雨,森林有泉有湖……
森林有詩。
要擺脫無名的羈絆,我最想走向森林;要拯救疲憊的靈魂,我最想走向森林;要吟唱隱秘的心曲,我最想走向森林。
花與樹的纏綿,雲與霧的交融,風與雨的相伴,泉與湖的交響,無處不是詩的流淌。雲聚雲散是詩,花謝花開是詩,草飛草長是詩,月圓月缺是詩。森林是詩的寵兒。
走向森林,常常是我的夢想,我的渴望。
在森林任何一個無人知曉的角落,都會有風吹落潮濕的種子。季節更替,在森林到處蕩漾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傾聽森林的語言,你將成熟,聰明,坦蕩,洞悉真理……生活的困惑與感傷隨風而逝。走在森林,你會發現你是快樂的,森林是無聲的呼喚,充實了你原本空洞的靈魂。
因為惰性和缺乏勇氣,我任從自己常年被囚禁在嘈雜的城市。城市也是森林。樓群像樹林,只是沒有枝葉沒有花朵沒有果實,沒有令人戀眷的狗尾巴草的清香。孩子們長大了,不會唱“採蘑菇的小姑娘”。樓群的顏色頑固,隱去了季節的界限;窗口在夜晚篩下星星,擠窄了無邊際的想像;鋼筋水泥傲然挺立,帶來了堅硬工具的壓抑。這是化工森林。在這裡,躺著的心事結成青苔,站立的思想競爭陽光,人們掩起私下里表情豐富的臉龐,讓善意和溫情在陌生中蟄伏窺望。
只有森林才會有真正的歌唱。森林的歌,嘹亮、清逸而深遠。森林裡最多的是樹,每棵樹都是歌手。
走進森林,走進歌聲,走進激動的曲調和流暢的節奏。帶著幻變的夢境,靈感和鳥語花香,離開城市的喧囂,演奏自己的樂章。讓漫天的音樂的羽毛,化作無邊的新綠與嫩黃。等待心靈的撞擊,等待靈魂的再生。
我見識過世界的不只一處森林。每次我都會力圖進入森林的深處。穿過茂密的、散發著濃郁的樹脂和草莓香味的松樹林,心裡泛起一種甜絲絲的快感。林中的湖泊像美人的鏡子,波光粼粼地閃爍在無邊森林的懷抱,映照著藍天的纖塵不染和青山的雄渾與嫵媚。
那些樹林是沒有獵人也沒有伐木者的。那裡的鳥是不害怕被人驚擾的。頭上樹椏上,這兒那兒站著不知名的鳥。它們大大方方、滿不在乎地站著。不時地懶洋洋地一跳。有時候落到離你很近的地方,然後又撲撲地飛起,它們撥起的風,直朝你臉上吹過來。柔順的,毛茸茸的松鼠就在附近無憂無慮地跳來跳去。有時候會突然停下來,蹲在離你最近的樹枝上和灌木叢中,睜大眼睛滴溜溜地打量你。所有的生靈都充分享受著作為這片樹林的天然主人的特權。
森林無疑有一種凝重的隱喻性質,暗示出生活最為深沉的一面。森林是生命的典範,告訴人們生命的原始法則。
潮濕的涼意從四面八方襲來。鳥悄悄地離開被太陽曬得溫暖的樹梢,振起翅膀,依戀地、默默地飛進樹林深處。霧在林中飄蕩。霧是半透明的。並不妨礙仰望樹縫中的天空。被樹枝分割的天空特別明亮。讓我想起南方家鄉閃爍的星光,被星光照亮的豐沛的河流、綠樹中的城市和織錦般的田地。讓我想起世上所有我經歷過的美好事物。萊蒙托夫說得不錯:“當我們遠離塵世而跟大森林接近時,大家都不由得變成孩子了,心靈擺脫了種種負擔,恢復了本來面目。”契訶夫是那般動情:“不可思議的大森林啊,你永遠放射著光輝,美麗而又超然,你,我們把你稱作母親,你本身包括了生與死,既賦予生命,又主宰滅亡。”托爾斯泰則給森林賦予了道德意義:“置身於這令人神往的大森林之中,人心中難道能留得住敵對感情、復仇心理或者嗜殺同類的慾望嗎?人心中的惡念應該在與作為美與善象徵的大自然接觸時消失。”當藝術家用圓舞曲為森林染上一片聖潔,“手風琴也打不破的寧靜”的抒情節拍展現著快樂與憂傷,有多少人已經如夢如幻,走進博大與深邃。如果有一天,你坐在森林之外的地方,夢想曾經的家園,你便會知道,失去綠蔭,靈魂就失去了庇護。混濁的噪聲從耳邊掠過,你將嫉妒並且哀怨,誰曾擁有過那片森林?
我多麼願意住在這樣的樹林:在森林幽靜的小徑徘徊,鼻翼裡全是青澀的氣味,看或枯或榮的草在夕陽下泛著柔柔的光,像長髮飄逸;在綠葉沙沙的伴奏下唱歌,唱消失的愛情和不可知的未來,聽或深或淺的水在林子的深處汨汨流動,像精靈呢喃。等有一天終於唱不出聲音的時候,就安靜面對樹葉的私語。風拂過思緒撥動迷離的眼神。捲起的紅松皮被陽光照耀,摘它一片,發現東風沉醉於此的秘密:暗香誘著彩蝶,在樹木之間傳遞著甜蜜。綠肥紅瘦都被遺忘,而你將保留森林中的這一縷暗香;等有一天終於不能呼吸的時候,就溶入樹下的泥土,無聲地悠悠地去到森林的漩渦深處,肅穆,莊嚴,神秘,而心,顫栗。然後在返青的季節,同螞蟻、蚯蚓和飛蟲、同所有卑微的生命一起,用柔軟的頭顱叩開泥土的門,迎接春天的來臨。一聲鳥鳴,心便永不寂寞。
草原
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你的眉頭像未解的結,你的腳步疲憊而蹣跚。
我把喧囂的城市留在身後,我把擁擠的人群留在身後,我把所有的躁動和衝撞留在身後。
把自己交給蒼茫。
你失落了什麼?你要尋找什麼?你想得到什麼?
我問藍天,我問大地,我問。
草原,向我張開博大的襟懷。從兩邊湧到路上來的、被露水淋得透濕的花枝和草棵子殷勤地拂著我的褲腿,像默默的愛撫。
古老而爛漫的草原。埋藏無數卜骨、陶片、斷簡、殘碑的土地;站立長城、寺廟、黯淡的宮閣和拓荒者廢墟的土地;橫亙叱吒風雲、如狼似虎的壯士演習殺戮的古御道的土地。
王朝的連營埋進深草;將軍的鹿角沒入沼澤。方尖碑如斷鍔。水泡子是飲恨蒼天的眼睛。從刀光火石到金戈鐵馬,從血流飄杵到冠蓋如雲,皆杳然如蒼狼嗚咽。帝王的霸業連同古戰場一起退出歷史,一個鞍馬部族的史詩在季節河道聲息乾裂。
而草原依舊。
高聳的大陸板塊空曠恆大,弓起球面的脊線。草原把最廣闊的空間留給七彩氾濫。芳草年年綠,碧色直鋪天涯。千萬種花如潮水,洶湧漫捲草原。乳汁洗出的天空,雲舒雲卷如峨峨高髻、蕩蕩裙裾。蒼鷹盤旋,大道似瀑布。
真靜啊。天地間是一片亙古的肅穆。遠遠的什麼地方,好像有人在動情地唱歌。那是幻覺。只有風,只有白樺林,只有不甘寂寞的杜鵑、野百靈和蜜蜂在私語。
思想就像徘徊在迷離草莽的孤馬,你會一再地想起那些似乎遙遠的、已經忘卻的過去,心裡無端地湧起一種莫名的、淡淡的卻是幽深的甜蜜或憂傷。你會感到好像早就有過這種體驗,要不就是做過一個和眼前的情景極為相似的夢。但是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是在一生中的哪個幸或不幸的時刻,你怎樣也記不起來了。生活就像流水一樣,淙淙地從你身邊流過,你失落了很多,卻不知道那是些什麼。
最遠的地方,熱浪蒸騰的高坡,號角悄然聳起。最初是一對,然後是一簇,然後是一片。然後,草原生命交響的高潮赫然君臨。
萬種天風驟然狂作。駿馬雄壯的肌群,突起為跳躍的峰巒。馬群縱姿跋扈,從遠方或更遠的遠方潮湧而出。
大宛汗血天馬從西極承靈威、涉流沙而來,從黃河負圖而來。與犁鏵一起耕耘生民的艱辛;與刀斧一起劃破凝滯的血海;與香車一起裝點貴冑的榮華。你為文明所依賴,你也為文明所駕馭;你為文明所恩寵,你也為文明所束縛。
什麼時候,文明放逐了你,文明又解放了你!
於是你重又成為草原的王者至尊。自由與奔放重又成為你的特權。鋪張揚厲的野性重又回到你的身上。天風滾滾,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像在旁啊,你重又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走雲連風,吞吐大荒。
狂舞的鐵蹄在我的血管裡奔騰,驚心動魄的轟響是冰河破裂一瀉千里。我忽然明白了我的沉重;我忽然知道了我的尋找;在地震般的顫栗和閃電般的快樂的瞬間,我忽然領悟了生命的開端和終結的全部歡樂和痛苦的奧秘:掙脫慾望的韁索,卸下誘惑的鞍轡,去呼應草原生命大氣磅礴的抒情,一種另樣的、博大的愛情——愛生活、愛生命、愛大地,直到永遠!
夜要來了,多情的落日在吐力根河對岸向草原告別。暮色像紫丁香,有一個騎手在火紅的天邊向遠方頂禮。
草原像人的心靈——當心靈純淨而充滿幻想,它就變得無比深邃——深邃得能容納整個世界。
我走在七月黃昏的草原,草原的路通向一切道路。遠處是遼闊明亮的地平線,身後是覺醒的腳印。
這一天多麼好!整個世界像在童話裡變了樣子。這樣的日子一生也許只能遇見一次。這樣的日子一生只要遇見一次。
感謝你,草原!感謝你金燦燦的光,藍湛湛的水,甜絲絲的風和轟轟烈烈的生命。
在怒放的花叢中盡情留連吧,在熊熊的篝火前盡情跳躍吧,在生命的潮水里盡情徜徉吧。火在顫栗,酒在燃燒,舞在踢踏,靈魂在響著黃鐘大呂的律動。當黎明再來,金子般的朝霞又會噴薄而出,我又將遠行,讓聖潔的大光明永照朝覲生命的虔誠。
湖泊
湖泊,上吞眾水而下哺巨流,大氣磅礴以波動日月。湖泊是“大地的眼睛”,看透了千年的滄桑。在湖泊操練的兵甲曾令天下四分五裂;在湖泊廝殺的豪強曾立江山於大一統;在湖泊洶湧的鮮血、浮沉的屍骨和縈繞不去的悲歌曾使歷史瞠目結舌;在湖泊駐足和歌吟過的有中國最優秀的詩人和文章家。湖泊是雲的故鄉,水的故鄉,生命的故鄉,神話、英雄和詩歌的故鄉。
湖上的無數島嶼,是鄉土社會的史書庫,漂浮在藍天一樣明亮和廣闊的湖面,正是我常常莫名地嚮往的島嶼,擁有著美麗、成熟、淳樸以及大自然超常寵愛的島嶼。立於樓頭,四面是粼粼發亮的茫茫湖水,點綴著鷺鳥翻飛的島子和機船上冒出的裊裊輕煙;樓下,夾在老屋和新牆之間的幽深村巷裡,響著當地盲藝人的古老弦子和漁鼓。如果說我曾在城市的生活中一度覺得親切卻陌生、虛榮但似乎不真實,那麼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這裡的人群陌生卻親切、也許缺少虛榮但真實可信。它遠不止是地理意義上的夢境,還同時是文學意義上的夢境,它就存在於現實中,還將存在於無數人的想像中。
湖泊是我永遠的精神故鄉。我的青春——人生最寶貴的年華,是屬於它的。我在湖泊播種希望,流了汗,還有血。生活,用巨大的、甚至是可怖的風暴和洪水,同時也用暖人的陽光和鼓動帆的風,粗暴而又溫柔、無情而又寬厚地鑄造了我的生命之舟。在那之後,我的關於歡樂與痛苦的最深切的經驗,我的最熱烈與最陰沉的情感,乃至我創作靈感的源泉、我的審美理想以及藝術追求的激情和情致,都是同它聯繫在一起的。
清晨,風在水上滑行,湖邊的泊船輕輕地搖動,偶爾撞出親暱的響聲。一隻水鳥在桅杆頂上打了個趔趄,翅膀散開來,拍了幾下,終於站穩。然後就神氣活現地站在那裡,不時勾下頭,啄一啄羽毛。
大白天,天和水在很遠的地方連接起來。天上一絲雲也沒有,水被天照出一片白亮,刺得眼睛生痛。不時有冒著濃煙的拖船拽著的駁船,和綴滿了補丁的絳紅色或土黃色的帆從那白亮上劃過。
薄暮時分,最遠的天邊,橫著條狀的金色雲霓。巨大渾圓的太陽在那條云霓上面若有所思地註視著將要進入黑夜的世界。一行雁筆直地向上揚著,在它面前緩緩移過。一片帆長久地在太陽的圓心處停著,凝然不動。淡淡的紫色的暮靄瀰漫過來,把湖罩在一片柔和明亮的光暈裡。
到了夜晚,霧氣一團一團在黑暗深處浮起,湖上的航標燈飄忽不定、時隱時現。然後,遠處越來越清晰地現出一些起伏不定的輪廓,那是對岸的山巒。漸漸地,山巒上的光亮越來越廣大,似乎有個人高挑著一盞雪亮的燈,正從容不迫地在山的那一面攀上來。那盞燈終於一點一點地從山脊露出,漫無邊際地照亮了幽藍的夜空。這是月亮。所有的星星都隱沒了,而在默然裡湧流的湖粼粼地閃起光來。湖邊的蓼草靜靜地擺動,偶爾響起魚躍的聲音。幾隻水鳥被驚起,拍著翅膀從草尖上掠過,又消失在另一片草叢中間。
數也數不清的湖汊,汊汊有人家。到夜晚,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村落,紛紛亮起燈火,跟滿天的星斗互相照應,讓你明明白白地入了夢境,分不清是星斗落在了湖里,還是燈火點在了天上。
湖上諸島,家家開門臨水,村民淳樸,古風猶存。浮於蕩蕩碧水藏於森森古樟中的漁村,時有若雨若煙、似有或無的弦索之響,絲絲縷縷的水韻芳馨,令人疑在一個遙遙舊夢。
湖泊的一切生靈皆被視為神物。生靈有知,也把湖泊當作了天國。夏候鳥白鷺是湖泊的王者。白鷺飛時,兩腳向後伸直,遠遠超過尾巴,兩扇寬大的翅膀緩緩鼓動,從容不迫,氣度非凡。白鷺是韻在骨子裡的詩,是樸素和高潔的形象化。麗日之下有白鷺翩飛,藍天便有了心跳的動靜;細雨來時水田里站了一隻兩隻白鷺,水田便成了一幅玻璃的畫框;山岩上有白鷺群立,山岩便登時有了蓬勃的生氣;夕陽里有成行白鷺低飛,更是鄉間日子的一種恩惠。而冬候鳥白鶴則更其壯觀。一個又一個從雲端鑽出的鶴群,長羽臨風,翩躚而來;長喙含雲,吟哦而來;長蹠踏浪,高蹈而來。漫天是驚心動魄的鶴舞和鶴鳴。遼闊明亮的湖面,躍動著千姿百態的鶴影,仙子一樣的尊貴,處女一樣的純潔,士大夫一樣的優雅。
霧氣在被雲霞照得斑斕的湖面悠長悠長地漂浮。遠山是一抹淡淡的煙痕。風吹著唿哨,在葦叢上掀起漣漪。隔年的枯草里,素淨的白蒿、翠綠的筅帚菜、肥碩的鐵掃帚、柔韌的馬鞭草和纖細的碎米花一堆堆地洶湧綻放。生命萌動的氣息四處瀰漫。湖灘上的鷺或鶴,對人視若不見,或埋頭在水里尋食,或專心啄羽毛,或昂首闊步高視徜徉。壯碩的水牛臥在草叢,與那些輕盈的鳥默契著,憨憨地眨著滾圓的眼睛。
哦——嗬嗬嗬嗬嗬嗬——
湖心有船起了呼號。船夫怡然,櫓似搖非搖,手指指點點。
湖泊遠離塵囂,澄澈透明,在一個環境日漸使人憂慮的世界,或許是最後的一泓清水,最後的水上香格里拉。
百年前的哲學詩人已然預感到人類必將重返故里,重返童貞。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還鄉就是返回人詩意地棲居的處所。人的內心,永遠存在著一個“故鄉情結”。那是一種溫暖的情感的凝聚,是無盡的夢幻和永久的魅惑。整個人生就是一次精神之旅,每一步都在尋找最終的故鄉,所有朝聖者的疲憊,都會被故鄉的煙火鍍亮。
湖泊的光芒穿透了生命的意義,湖泊是精神生命的原點。湖泊是雲、水、陽光孕育的驕子,而我願是魚,是鳥,是水柳,是爬滿島嶼的白蒿、馬鞭草和碎米花。我將為水的靈魂所吸引,依靠著帆在風雲間行走,從路途到心靈,從喧鬧到安靜,張開雙臂,去擁抱自然,去與鄉親交談,去聆聽最質樸也最靈動的語言,去享受最真實的美。是的,如果我們改變不了生命的長度,那麼我們何妨拓展生命的寬度。
河谷
峻峭的河岸上,星羅棋布的村寨綴滿了海拔千米的山坡。山脊懸空的巨石,古碉和煨桑塔矗立,那是生殖崇拜的象徵。整座村寨都處在它的威儀之下。觸摸著它粗糙的肌膚,彷彿觸摸一個久遠的符號。神靈已經在雪山上生活了幾十個世紀,一個民族原始的思維構架倚山而立,暗示著時間的悠遠。它們是生命和美麗的保佑者,這是一種執著的堅守,守望靈魂永恆的驛站。
村寨的女人,花頭帕,紅長裙,古韻悠然,優雅端莊,一如從遠古款款而來。風中飄動的鮮豔裙擺,如同對面綿延的山勢此起彼伏。歷史的流風遺韻與現實的千嬌百媚交織成迷幻的夢境。
埋藏得太久的河谷,揭開羞澀的面紗,以嬌豔的盛妝,捧出撩人的風情,給世界一個驚豔的姿勢。寨子的煙囪裊裊炊煙升起,寺廟甦醒的法號低沉而悠遠,不知名的萬紫千紅爛漫綻放,傾聽背水女孩胸前清脆的鈴鐺。
深深的河谷,從昨日禁錮的古堡吹奏出世外的天音。
山腳下翻騰的河水,無聲地咆哮,看上去平靜異常,流淌在太陽、月亮、白雲、雪山、土地、青稞、勞作、酒碗以及睡夢中,只有仔細諦聽,才能得到時間深處的消息。河谷蟄伏於雪山深處,延續著古老的民俗,時間與空間神異結合,成為真正的世外桃源。疊翠的山巒,湍急的河流,黑色的碉樓,潔白的石屋,頭帕與長袖,篝火與舞蹈,演繹著河谷兒女自在的日子。
那個傍晚最讓我動容的是晚飯時見到的端茶壺的女孩。在那間色彩斑斕的木屋裡,她帶著幽谷的清香緩緩從客人身邊走過,給所有人上過茶,便靜靜地把銅壺擱在窗台,然後倚窗而立。她的心一定在輕輕跳動,彷彿初戀的震顫從月色中傳來,而情歌就在手上的銅壺裡翻滾。
窗外,也寂靜也燦爛也冷清也溫暖,不知從哪里傳來琴弦的撥動,弦韻為煮茶的暖煙滋潤。女孩高高的鼻樑上的大大的眼睛迷離而潮濕,柔潤的小手無端拂拭已經錚亮的銅壺,似乎在翻閱漸漸成長的情懷。輪迴重複的安寧與恬淡的歲月,填滿了希望的華年。一行行來自遠古的歌謠,一陣陣行雲流水般湧進鼓脹的心房。
直到今天,我覺得自己依然留在那條河谷,沉醉在最初的花香氾濫的黃昏。我希望自己每天傍晚都能夠在那間斑斕的木屋裡飲茶,看著那個端茶的女孩在窗邊默默地佇立,像飄在雲朵上的一個遙遠的花的剪影。
我的文學觀
讀文藝史,我敬重的是那樣一類藝術家,即他們創作的表達與他們的人格,與他們所表達出的價值觀和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好惡、愛憎是一致的。我喜歡的藝術家,他的人格是剛直不阿的,他的創作表達帶有宏偉的氣魄。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但事實上也未必一定有言,作者的人格很高尚,作品就一定好?這也不一定。所以,不如這樣說吧,如果人格很高尚,作品成就也很大,這是第一流的藝術家,也是我最敬仰的。
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我認為至少應該具備兩個條件:一方面,給一代人、給一個時代提供了一種至高的思想視野,把我們整個眼界和心胸展開到一個非常廣闊的程度;另一方面,藝術表達有開創性,藝術家的思想能力所達到的高度是他同時代的人所不能達到的。他的表達給後世的藝術家提供了最好的範本。偉大的紀念碑式的人物的產生決不是隨意的,而是時代和歷史選擇的結果。我們可能永遠達不到他們的高度,但我們可以崇尚他們,景仰他們,努力去接近他們,使自己的工作變得有意義。
藝術家應該是“靜”的。就是那種“小徑容我靜,大地任人忙”的“靜”;那種“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的“靜”。 “靜”是一種境界,能不能“靜”下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藝術家的命運。偉大的作家首先是有“靜心”的作家,他是生活的思考者,生活的評判者,當然也是生活的參與者。面對著紛繁複雜的變化的世界而沒有“靜心”,那就只能隨波逐流。 “靜”是指內心的“靜”,內心沒有躁動,沒有過分的慾望,唯一所做的就是靜靜地觀察,靜靜地思考,靜靜地表達。整天躁動不安、費盡心機不拿這獎那獎誓不罷休的藝術家,其作品到底有多少藝術含量是一件很可懷疑的事。
一個藝術家整天忙於給自己塗脂抹粉,搔首弄姿,肯定是徒勞。真正的藝術家,為藝術生,為藝術死,不會屑於在媒體上保持自己的新聞性,讓自己成為一個明星。恰恰相反,他會努力避開世俗的紛繁。真正的好作品,可能一時得不到重視,但最終不會被忽視。沉得住氣,就會有好作品,大作品,大藝術家。
| < 前一個 | 下一個 > |
|---|
- 2011-05-15 - 泰戈爾對話愛因斯坦:真理是真實的嗎?那美呢?
- 2011-05-08 - 為什麼專制帝國的改革難以成功?從清末新政失敗說起
- 2011-05-06 - 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題材與文人心態
- 2011-01-23 - 坦然面對死亡 - 大同歷史名人李少蘭
- 2010-10-09 - 光明日報:東西美學的邂逅——中美學者對話身體美學
- 2010-08-19 - 大歷史觀宗師 黃仁宇先生 詳細介紹
- 2010-04-05 - 文懷沙現身武漢自嘲:我是什麼大師?狗屁!
- 2010-04-05 - 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國學大師的荒誕人生
- 2010-02-14 - 老不糊塗:羽扇綸巾葉劍英不亂情場定乾坤
- 2009-12-12 - 成功靠天靠地靠自己(俞敏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