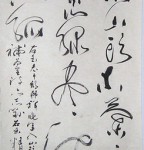| 文章索引 |
|---|
| 從史籍無聞到“天下第一行書”——淺析唐太宗對《蘭亭序》的“接受過程” |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註釋: |
| 所有頁面 |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永和九年暮春,文人雅士興會蘭亭妙地,吟詩作賦,曲水流觴,詩成之後,王羲之戛戛獨造,以一篇《 蘭亭集序》驚座四方,由此創造了東晉書法史上的奇蹟,而且構築了““天下第一行書 ”的千年佳話。絲毫不誇張地說,東晉以降的書法現象總能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蘭亭”的光芒。
然而如果一味地稱頌《蘭亭序》的偉大,而冷落了唐太宗的“睿賞”,似乎並不合情理,正如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所言,藝術作品本身“是存在於所有變遷著的存在體之中的,這所有存在體是作品本身的組成部分,它們與作品本身是同時並存的”[2]。因而從這一意義上探討唐太宗對於《蘭亭序》的接受問題,對於我們書法史的學術建構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了。
一
著名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德國接受美學家姚斯曾指出,“文學作品並非是對於每個時代的每個觀察者都以同一種面貌出現的自在客體,……只有閱讀活動才能將作品從死的語言材料中拯救出來並賦予它現實的生命”[3]。書法作為一個精神圖像化的文本,也同樣符合上述規律。王羲之的書法就經歷著這樣一個不斷被闡釋不斷被“生成”的過程。早在羲之生活的東晉時期,他的書法就已揚名四方,所謂“聲華四宇,價傾五都” [4]。不論是上層士人“桓玄耽玩不能釋手”、“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家贏金幣,競遠尋求”,還是平常老嫗“復以十數扇來請書”[4]都著實說明羲之書法雅俗共賞,眾人寶愛。不僅如此,羲之書法已為時人效仿,有時竟連右軍自己都說“小人幾欲亂真”[5]。但是從羲之仙逝後到南齊之間,大令書法的豪放之美更加為人推崇。儘管如此,王羲之作為偉大書家的地位卻始終不可置疑。對此,書論中處處皆有明證:“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隸。羊欣雲'古今莫二'” [6];南朝宋虞和雲,二王書法“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7]到南朝梁武帝蕭衍時,羲之不及獻之的局面大有改觀,“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8]與此相應的有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中列王羲之為“上之上”品,而王獻之僅為“上之中”品。效法羲之書法的現像在此時更加普遍,“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體,故是書之淵源。”[9]……筆者之所以做出如上枚舉,旨在把羲之書法從產生到唐代之前的接受線索做出大致梳理;試圖在鉤沉史料之際進行深入思考:既然“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11],既然他的書法已廣為流傳,那“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 [11]而令羲之“聞而甚喜”的《蘭亭集序》為何遲遲沒人提及,是文獻散佚還是尚未為人所重?
二
唐人何延之《蘭亭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羲之)揮毫制(蘭亭)序興樂而書,……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珍愛寶重,留付子孫傳掌”[12]。原來羲之珍愛《蘭亭》,不願其流落它所,僅限家傳。如此這般,傳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時,《蘭亭序》不得已傳給其弟子辯才。辯才自得《蘭亭》,深藏秘室,十分寶愛,然而他的小心翼翼還是未能保證《蘭亭》保持“平凡”的命運。
貞觀年間,唐太宗登基即位。這個馬背上驍勇善戰的皇帝深知“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13]的道理,於是蓬勃興起一系列整齊文化的措施。在他大興儒學、張皇文統,建立新的教育和選舉制度之時,所謂“身言書判”的“書法”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視。馬宗霍在《書林藻鑒》概述道:“考之於史,唐之國學凡六,其五曰書學,置書學博士,學書日紙一幅,是以書為教也。又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其三曰書,楷法遒美者為中程,是以書取士也。以書為教仿於週,以書取士仿於漢,置書博士仿於晉,至專立書學,實自唐實。”同時,太宗又“詔京官職五品以上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案中書法以授之。”[14 ],除推行上述書法政策之外,太宗還定立王羲之為國人的學書偶像。他“於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昭購求,殆盡遺逸”[15];“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 [16 ]到貞觀六年太宗“命整理禦府古今工書鐘、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16],在這千餘張真跡中,卻惟獨沒有《蘭亭序》,一場聲勢浩大的懸賞《蘭亭》的活動由此展開。
唐太宗得到《蘭亭序》的過程,有兩種不同的記述。其一為《劉餗傳記》的記載:“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其二為何延之《蘭亭記》的記載:“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嘗於所寢方丈樑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寶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齎優恰……方便善誘”。面對赫赫皇權,辯才牢記先師的遺願、恪守自我的誓言,“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然而太宗渴望《蘭亭》迫切之至,竭盡所能,命令“負才藝,多權謀”的大臣蕭翼喬裝打扮,和辯才結為朋友,最終智取蘭亭。這第二種記載富有傳奇色彩,歷史上廣為流傳。雖然可能是歷史史實的文學化渲染,具有“歷史神話學”的意味,但它的形成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足以見出太宗對羲之有多麼崇拜。
其實,據《劉餗傳記》記載,隋煬帝見過《蘭亭》真跡,“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所得,至大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這位同樣喜好書畫雅樂的帝王卻沒有對《蘭亭》產生好感,僅以“王不之寶”留給後人無限遙想,在不輕易間把“第一讀者”的身份拱手相讓。何為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它當然並非第一個接觸藝術作品的讀者,而是在藝術接受活動中對經典作品的首次權威性的解讀者,借用陳文忠先生的話說,“所謂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是指以其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闡釋,為作家作品開創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礎、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讀者”[17]。具體到《蘭亭》而言,唐太宗責無旁貸地擔當起“第一讀者”的神聖使命,正是他的出現,讓《蘭亭》的接受史變得光怪陸離。假如離開了唐太宗,《蘭亭》會在何時又會被怎樣接受,都是無法設想的。
三
唐太宗畢竟是珍愛《蘭亭》的,他“寶惜者獨此書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賞”[18]。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所甚焉”,《蘭亭》的摹本和臨本應運而生。 “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19],這是著名的“馮摹本”即“神龍本”。另外還有傳為虞世南臨本“天曆本”或“張金界奴本”(蘭亭八柱第一)、傳禇遂良摹本(蘭亭八柱第二)、傳禇遂良臨本(黃絹本)以及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的《定武蘭亭》等。 [20]
對於《蘭亭》的鍾愛之情,太宗不僅限於把玩真跡,而且付諸於“心摹手追”的臨池實踐。從現存的《晉祠銘》、《溫泉銘》、《屏風帖》以及《淳化閣帖》收入的太宗書札來看,無不體現出他對羲之書風的吸納和發揚。
品評羲之書風常以“內擫”一詞作以形容。沈尹默在《書法論叢》中指出:“要用內擫法,先須凝神、靜氣,一心一意地註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心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力十足,剛勁不撓。”可見這是一種剛堅而中正,流美而寧靜的書風。太宗赫赫有名的《晉祠銘》就取法於尚骨力的“內擫”法。此書多用圓筆藏鋒,飽藏骨力,千鈞之力凝聚毫端。在《石墨鐫華》中趙函評論此碑“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無獨有偶,清人錢大昕評曰:“書法與《懷仁聖教序》極相似,蓋其心摹手追乎右軍者深矣。”選取《晉祠銘》和《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中相同的字做出比較,其淵源關係便非常明顯。以“承”字為例(圖一),不難發現兩字的運筆都為“內擫”法,其字勢也十分相似,只是《晉祠銘》的“承”字生動、跌宕一些,而《聖教序》的“承”字更平正一些。再以“哲”字為例(圖二),其運筆的內在理路也大體一致,且都重骨力,但《聖教序》中的“哲”字在行筆中更注意提筆,因而更顯力度。比較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太宗取法於羲之的運筆和結體,但其造詣畢竟不及右軍,不免顯露出運筆的浮軟和結體的散漫來。另外,《晉祠銘》中三十八個各有千秋、絕無雷同的“之”字著實可與《蘭亭》變化豐富的“之”字顰美。從整體佈局而論,李書既保留王書字字成其勢,互相映帶的章法特點,也體現出北書嚴整緻密的佈局,從而顯得莊重而穩健,秀雅而渾厚,溫潤而雄放,形成了內剛外柔,南北兼具的風格特點(圖三)。
如果說《晉祠銘》反映出太宗性格中求實沉著的一面,那《溫泉銘》(圖四)則更多的是其風流倜儻的明證。此書通篇流溢出一種虎步龍行,豪放不羈的帝王氣概。它把《蘭亭》(圖五)用筆的灑脫自然、抑揚流轉和章法的疏朗通透與帝王的英邁之氣融為一體,在雍容和雅,圓勁遒麗之外,更具有整勁奔放之勢,不乏劍戟森嚴之感。所謂“質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總法體。”[21]再以《淳化閣帖》中收入的《兩度帖》(圖六)為例,論其章法,行氣貫通,上下呼應,左右欹側,跌宕之致實為右軍手札之後續。總之,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傳承與闡釋是顯而易見的。宋人張耒在《宛丘集》中說太宗書法“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誠非虛語。
唐太宗不僅在實踐領域承傳羲之書法,還專門寫了《王羲之傳贊》大張王學。在該文中,太宗指出鍾繇書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古而不今”,“長而踰制”;獻之書法“字勢疏瘦”,“筆踪拘束”;子云書法“無丈夫氣”;而唯有羲之書法“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 [22]至此而給予羲之書法一個絕對的歷史定位,使其書法地位從晉宋間特重獻之,從梁武帝“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鍾繇”[23]的低谷中躍然走出,成為引領中國書壇的千年盟主。
“盡善盡美”是書法審美的最高原則,唐太宗之所以加之王羲之,是因為他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是崇尚骨力和沖和之美的最佳結合。 “骨”的概念最早由衛夫人在《筆陣圖》中提出:“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在此,太宗排抑梁、陳俱肆巧媚、缺乏典重的書風而強調書法之筋骨,實有矯正南朝浮靡書風的目的。在《論書》中他極大地突出骨力的地位:“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在尚骨的同時,太宗反复提出“沖和”的要求。如“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志氣不和,書必顛覆……正者,沖和之謂也”,[24]“神氣沖合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鋩,用鋒鋩不如沖和之氣” [25]等。沖和是一種平和典正的氣象,它最早源自《老子•四十二章》“萬物光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黃鉞《二十四畫品》中也有“沖和”一品,“在書法美的領域裡,沖和具有虛靈平和、沖淡蘊藉的品格,它意志靜穆,境界深遠,舉之可見,求之已遙……在晉代,王羲之最富於沖和之氣”[26]。在此,太宗的論書主張可與一代英主政治上兼容並蓄、審美上融合南北的取向互相印證。
四
在藝術作品的接受過程中,正是“第一讀者”的引介才使藝術作品煥發出勃勃生機,“第一讀者”深刻地、突破性地、頗具洞見的認識無疑是藝術文本接受史上最為閃亮的一環。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對於同一作品的“召喚結構”,不同的接受個體在不同“期待視野”的引領下會產生個性化的解讀,這對於藝術作品的原汁原味無疑是一種消解。在“第一讀者”以其優先性地位的接受影響著後來者的理解時,我們就不得不思考:若將藝術作品回放於整個藝術史的長河中,“第一讀者”的接受是否會對接受史的總體流變產生重大的影響?進而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因太宗的推崇,“貞觀、永徽以還,右軍之勢,幾奔天下”[27],遂有“虞世南得其美蘊”、“歐陽詢得其力”、“禇遂良得其意”和“薛稷得其清” [28]的說法。禇遂良《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把《蘭亭》列為右軍行書第一;孫過庭《書譜》中“……《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 、《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也都體現了時人對《蘭亭》的仰慕之情。筆者應予指出,《蘭亭》的蔚為風氣並非僅限於朝廷內部和士大夫階層,它自“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29]而流落民間之後,立即具有廣泛的接受群體,否則,敦煌卷子中怎會出現唐經生所書的《蘭亭》寫本? [30]時至宋朝,《蘭亭》再度進入了接受高潮:趙宋帝王宋太宗、宋高宗都熱衷王書,特重《蘭亭》;北宋四家“蘇黃米蔡”和南宋姜夔也非常喜愛《蘭亭》,尤其是“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31],用功甚勤;加之自《淳化閣帖》產生後掀起了刻帖高潮,《蘭亭》的刊刻也十分風靡,“ 《蘭亭》帖,當宋末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 [32];而《蘭亭考》、《蘭亭續考》等“《蘭亭》學”專著的問世再度提升了《蘭亭》接受的理論層次。進入元代,趙孟頫一生學《蘭亭》,他的《蘭亭十三跋》是當時《蘭亭》接受領域中引人注目的現象。明代是又一個崇尚帖學的時代,明成祖喜文好書,明仁宗也留心翰墨,曾臨《蘭亭》賜予沈度。清朝的幾朝皇帝也雅好翰墨,康熙帝有時竟日臨《蘭亭》數遍;乾隆帝曾禦定《蘭亭八柱帖》。明清的文人雅士也極度推崇《蘭亭》,如董其昌給予《蘭亭》很高地位,“右軍《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33]。而明人陳鑑在為“米元章題《禇摹蘭亭》”的跋語中寫到:“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最終確定了《蘭亭》“天下第一行書”的神聖地位,“《蘭亭》一序,遂如日月經天,千秋萬世,照耀壇坫矣”[34] 。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曾說,唐太宗“既不是一位複雜的人物,也不是一位有才能的詩人,而是一個更成功的統治者。存世的太宗詩集是這一時期最大的集子之一。儘管有作為詩人的局限,他仍然明顯地註重技巧。在統治前期,他似乎既鼓勵儒家的教化,也提倡宮廷詩的雅緻,不偏不倚地接受二者,認為它們都適合於帝王的尊嚴。”[35]以上側重講對詩歌的改造,置換到書法領域也互為表裡。太宗之所以如此珍愛《蘭亭》,其個人好尚當然不容否定,但更深層的原因應來自帝王“王道”話語機制之下的“伎倆與陰謀”。 《蘭亭》不激不厲、風規自遠、文質彬彬的審美取向暗合了太宗一朝天子汲汲用儒家“溫柔敦厚”的思想歸整人心的強烈願望;他之所以飽含深情地撰寫《王羲之傳贊》,給予“書為小道”時代中的書家以如此禮遇,是他積極利用羲之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以求得到更大的社會支持;是他政治意志和個我追求的另一形式的宣示和強調;是“王聖同體”制度下君主遵從“責任倫理”的必然取向。因此,太宗雖放眼羲之,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現實內涵要遠遠大於其歷史內涵!因而,唐太宗所擁有的《蘭亭》文本已與載著騷人遺韻、晉宋風流的《蘭亭》客體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作為接受者一方的他,最初就帶有一種“先行之見”[36]的“前理解”而進入作品,這必然會引起“初始視域”與“現今視域”的錯位與融合。唐人在這“視域融合”後的語境中認識《蘭亭》,必然會受“第一讀者”接受的影響。於是在一片頂禮膜拜的喧嘩聲中,在認同權威心理的驅使之下,《蘭亭》被無限地臨摹、複製、神化,它的神聖光環日見增厚,它的無言法力輻射千載,逐漸由藝術文本淪為政治工具,最終導致了《蘭亭》接受的“效果歷史”始終帶有幾分虛幻,幾分神秘和幾分無奈,甚至引來後代的質疑……
當然,話又說回來,借助政治力量推動的“崇王”運動,如果沒有深厚的歷史與美學作為支撐,它必然曇花一現。 《蘭亭》的藝術價值不應因政治的介入而遭受非歷史的貶損。今天當我們再來審視這一千古名作,它那內擫的筆勢、遒麗爽健的線條、圓融的體態盡顯羲之書法的風流;它是骨力寓於姿媚之中,匠心蘊於自然之中的傑作;是玄學氛圍濡染下羲之放浪形骸的精神氣象之反映。因此僅就其藝術文本的獨立價值而言,也完全配得上太宗褒獎,也完全有資格登上中國書法史上的“至尊寶座”!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回想那個洋溢著天然情趣和活潑生機的《蘭亭》,不禁感懷,《蘭亭序》之遇唐太宗是福是禍,王羲之在天之靈是喜是悲,更與何人說!
註釋:
[1] 王羲之:《蘭亭詩二首》,載逯欽立編《先秦漢魏南北朝詩•晉詩》十三卷,中華書局,1983,第895頁
[2] [德] 伽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第175頁
[3 ] [德] 姚斯:《文學史向文學理論的挑戰》載蔣孔陽《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第435頁
[4] [5] [7] 虞和:《論書表》,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二卷
[6]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一卷
[8] 蕭衍:《古今書人優劣評》,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81頁
[9] 顏之推:《論書》,載崔邇平編《歷代書法論文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第28頁
[10 ]袁昂:《古今書評》,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二卷
[11][22] 唐太宗:《王羲之傳》,載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第2093頁
[12] [19] 何延之:《蘭亭記》,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三卷
[13] 劉呴:《舊唐書•音樂志》,中華書局,1975,第二十八卷
[14] 歐陽修:《新唐書•百官志》,中華書局,1975,第四十六卷
[15][29]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三卷
[16] 《唐朝敘書錄》,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四卷
[17]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第64頁
[18] 李綽:《尚書故事》載《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2739卷
[20] 注:因為本文並非考證文章,關於《蘭亭》不同臨摹本的書寫者問題仍沿用舊說。
[21] 竇臮:《敘書賦》,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五卷
; [23] 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三卷
[24] 李世民:《筆法決》,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117頁
[25] 李世民:《指意》,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120頁
[26] 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第664頁
; [27] 馬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1984,第237頁
[28] 李煜:《書評》,載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第一百二十九卷
[30] 《敦煌寶藏》第122冊第2544號
[ 31] 黃庭堅:《山谷題跋•跋東坡墨跡》,上海遠東出版社,第134頁
[32]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
; [33]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評法書》,上海遠東出版社,第25頁
[34] 祝嘉:《書學史》,成都古籍書店,第64頁
[35] [美] 宇文所安,賈晉華譯:《初唐詩》,三聯書店,2004,第42頁
[36] 注:以下術語來自[德] 伽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 < 前一個 | 下一個 > |
|---|
- 2013-12-29 - 巨人毛泽东百二十诞辰: 丁仕美草书“毛诗词”网上大展之前言
- 2013-06-24 - 字為心畫:氣韻藏於筆墨
- 2011-03-29 - 《法書要錄》十卷, 唐張彥遠撰《卷一》
- 2011-03-15 - 造字雜說
- 2011-03-15 - 天人合一與中國書法
- 2010-12-30 - 嶺南書法叢譚
- 2010-12-24 - 甲骨的終結與甲骨文書法的藝術轉換
- 2010-12-23 - 論用筆與結字:書法藝術成熟的三大歷史階段
- 2010-12-23 - 行書書論析要 - 歐陽中石
- 2010-12-20 - 漫談中國書法之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