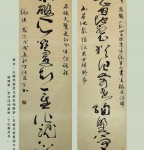| 文章索引 |
|---|
| 北島:中國詩歌應該遠離革命與宗教 |
| 第二頁 |
| 所有頁面 |
北島:談論詩歌,我們需要不同的時間尺度,從《詩經》到現在已有三千年了,按這個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麼。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面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個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面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它們。市場是圓的,無人稱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會說,照他看來,是公道的。或許如此。不過它是瞎子和聾子,既不愛文學也不愛冒險,不知也不會選擇。它的審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沒有思想。它只知價格,而不知價值。”帕斯的話正好概括了這二十年中國藝術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的外在危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內在危機,那就是我們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於心計,缺乏一種天真無畏的“少年精神”。這一點恰恰從內部消耗了向前推進的動力。
“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儘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不久前參加“香港詩歌之夜”的美國著名詩人蓋瑞·施耐德在香港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一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面?
北島:施耐德說的有道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復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十年前,北島離開故土開始了海外漂泊之旅,從歐洲到美國,寫詩之外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壓力和困頓。也許,這才是詩人的正常生活。兩年前,北島終於在香港安定下來,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去年3月,我在香港參加一個文學論壇,坐在北島旁邊,看著他默默批改學生的詩歌作業。
上個月,北島還把他全世界的詩歌朋友拉到了香港,為香港人民帶去了一場“香港詩歌之夜”的系列朗誦會。在香港這樣一個完全商業化的城市定居、寫作,北島覺得“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穫”,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兩個月前,北島獲得了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夫人甘琦女士代其領獎並發表缺席演講——“缺席”成了他與內地文化界聯繫的紐帶。在那次缺席的演講中,北島指出了當代漢語詩歌在過去以及現在遇到的困境。在北島看來,四十年前的中國地下詩歌是“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但四十年過去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漢語詩歌再度危機四伏。……詞與物,和當年的困境剛好相反,出現嚴重的脫節——詞若遊魂,無物可指可托,聚散離合,成為自生自滅的泡沫和無土繁殖的花草。詩歌與世界無關,與人類的苦難經驗無關,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機更可怕。”
“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
您目前因為各種原因,只能在香港寫詩創作,在這樣的狀態和環境中創作,帶給您意想不到的收穫是什麼?
北島:其實詩歌創作跟環境沒什麼關係。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穫:由於香港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與國際地位,由於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比如,剛剛結束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就是證明: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推廣非商業化甚至反商業化的“陽春白雪”,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說是成功的。所謂“絕處逢生”,就是這個道理。
您那一輩出來的著名詩人,這些年在創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滯,他們有詩歌之外的事業,您覺得他們遇到的困境又有哪些?
北島:寫詩難呀——可以這麼說吧,你每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熟能生巧。當然有些是寫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難處。
在這轉型的時代中,中國詩歌能發揮的作用會是什麼?
北島:這個問題應列入國家的五年、十年計劃中。不管時代怎麼轉型,詩歌都應該倖存下去,也必須倖存下去,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靈魂。
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說,詩歌是介乎宗教與革命之間的另一種聲音,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詩歌在中國(1949年以後的詩歌)哪個時期可能比較符合這樣的界定?為什麼?
北島:我先說明一下,這是他的論文集《另一種聲音》中的最後一篇,寫作時間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眾所周知,1989年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帕斯這樣寫道:“我們經歷著一場時代的轉折: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回歸,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義上的回歸。一種向源頭的回歸,同時也是一種向初始的回歸。正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不能親臨歷史的終點,而是親臨一種新的開始。被埋葬的現實的複活,被遺忘和被壓抑者的重現。正如以往歷史上發生的那樣,匯入一種再生、向初始的回歸幾乎總是混亂:革新,復興。”而帕斯認為,詩歌為這種回歸提供了可能。回顧人類歷史,宗教與革命帶來太多血腥的記憶,在這一意義上,詩歌是“另一種聲音”。談到1949年以來的這六十年,真正可以稱作“另一種聲音”的是始於上世紀的中國地下詩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並產生巨大的影響。其實這就是帕斯所說的那種回歸,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
在您看來,詩歌特別是中國詩歌應該離革命和宗教遠一點還是更近些?
北島:我認為中國詩歌恰好應該遠離革命與宗教。在我看來,革命與宗教有某種共性,那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並依賴組織甚至武裝力量來完成改造人類的目的——“存天理,滅人欲”。而詩歌不同,它純屬個人的想像,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強制性與侵略性。
四十年前的詩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否,既是起點,但沒走幾步就已經是終點了?這是不是您這輩詩人始料未及的?
北島:談論詩歌,我們需要不同的時間尺度,從《詩經》到現在已有三千年了,按這個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麼。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面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個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面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它們。市場是圓的,無人稱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會說,照他看來,是公道的。或許如此。不過它是瞎子和聾子,既不愛文學也不愛冒險,不知也不會選擇。它的審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沒有思想。它只知價格,而不知價值。”帕斯的話正好概括了這二十年中國藝術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的外在危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內在危機,那就是我們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於心計,缺乏一種天真無畏的“少年精神”。這一點恰恰從內部消耗了向前推進的動力。
“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儘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不久前參加“香港詩歌之夜”的美國著名詩人蓋瑞·施耐德在香港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一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面?
北島:施耐德說的有道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復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 < 前一個 | 下一個 > |
|---|
- 2010-12-24 - 甲骨的終結與甲骨文書法的藝術轉換
- 2010-12-23 - 論用筆與結字:書法藝術成熟的三大歷史階段
- 2010-12-23 - 行書書論析要 - 歐陽中石
- 2010-12-20 - 漫談中國書法之文化精神
- 2010-08-27 - 《書法述要》 陸維釗
- 2010-01-10 - 關於“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幾點感想
- 2009-12-02 - 淺析書法演進理路
- 2009-11-03 - 淺談書法的藝術神韻(轉載)
- 2009-10-10 - 對話朱守道、李一:論中國書法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 2009-09-02 - 巨型篆字“水”築上中條山的“理論”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