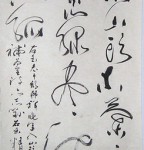| 文章索引 |
|---|
| 關於大巧若拙美學觀的若干思考 |
| 一, 拙是超越機心,達到偶然的興會。 |
| 二. 拙是超越機巧,達到天然的契合。 |
| 三, 拙是對機鋒的蕩滌,推崇淡然的美感。 |
| 四, 拙是生命存養之方,強調回復生命的本然。 |
| 註釋: |
| 所有頁面 |
二. 拙是超越機巧,達到天然的契合。
大巧若拙作為一個哲學命題,思考的中心問題是人工技巧和自然天全之間的關係,它是中國哲學中較早的對技術主義進行批判的代表性觀點。
《莊子》中從超越機巧的角度,談大巧若拙:“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6] 技巧的發展,是文明進展的重要標誌之一。在道家哲學看來,文明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並不必然帶來人的性靈解放。工具的發達,技巧的凝聚,技術方式的變革,由此基礎上產生的對技術主義的迷戀,卻構成了對人自然真性的壓抑。莊子認為,人類文明就是追求巧的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人常常會忘記,巧只是工具上的便利,並不能解決人心靈中根本的問題,物質的巧並不能代表生命的體驗。就像在工具理性發達的今天,人們有一種“文明空荒感”一樣。道家提倡大巧若拙哲學,就是將人從知識的躍躍欲試拉回到天全的懵懂;由慾望的追求返歸性靈的恬淡;從外在感官的捕捉回到深心的體悟。
莊子曾就庖丁解牛的故事,提出技進乎道的觀點。技是知識的,工巧的,而道是天成的,是生命的圓融境界。 “技進乎道”的“進”,不是說道超過了技,而是說道是對技的超越、否棄和消解。道,就是拙。在著名的梓慶削鋸故事中,有一段關於“術”的對話,梓慶削木為鋸,有鬼神難測之妙,魯侯就問他:“ 子何術以為焉?”他回答說:“臣工人,何術之有?”削木為鋸,當然是一種技術性的工作,但這位工匠卻否認這一點。他有自己的解釋:“臣將為鋸,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鋸,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他所獲得的神妙莫測能力,不在技術性,而在心靈的齋戒滌蕩,最終達到“以天合天”的境界,這裡沒有人工之巧,只有天地之巧。得道的過程不是技術積累的過程,而是養生的過程,養成內在生命的和諧圓融。
大巧若拙反對技術至上的思想,其核心是反對人為世界立法。在人為世界立法的關係中,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握有世界的解釋權,世界在人的知識譜系中存在,這是一種虛假的存在。大巧若拙哲學,是要還世界以真實意義——不是人所給予的意義。
大巧若拙,作為中國美學的獨特秩序觀,不是依人理性的秩序去解釋世界,而是以天地的秩序為秩序。如中國造園藝術的最高原則是“巧奪天工”,世界具有最美妙的秩序,人的一切努力就是悉心體會這樣的秩序,去除心靈的粘滯,去契合它。用明計成《園冶》的話說,就是“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園林創造“ 雖叨人力”,但“全由天工”。園林是人的創造,是人工的,但園林的人工,強調無人工刻畫痕跡,做得就像自然固有的一樣,做得就像沒有做過一樣,這就是天工。不是“人飾”,而是“天飾”,才是中國園林的立園之本。
西方傳統園林有一個內隱的原則,就是人是自然的主人,重人工,重理性;中國園林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的密合成為造園的根本原則。西方傳統的英式園林、法式園林,或是羅馬式園林,都強調外在整飭的秩序,要求對稱、整齊,符合其追求理性的趣味。但在中國則重視美麗的無秩序,力求體現大自然的內在節奏,表面上的無秩序隱藏著深層的秩序。剷平山丘,乾涸湖泊,砍伐樹木,把道路修成直線一條,把花卉種得成行成列,這是西方園林的創造方式。而中國園林強調的是“天然圖畫”。中國園林是造“曲”的藝術,多用曲線而少用直線,一灣流水,小亭翼然,小丘聳然,加之以灌木叢生,綠草滿徑,雲牆,迴廊,潺潺的小溪,體現出強調的野趣——自然本來的趣味。像江南園林的雲牆,如綿延的長龍橫臥於一片青山綠水之中,別具風致。
排斥技術主義的思想,在傳統美學中是占主流的。中國藝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形神、氣韻論為人所重視,重天然輕技巧的傾向就已初露面目。此時書論中提出天然、人工的分野,強調“天然”的穎悟,認為此一能力乃“神化之所為,非世人之所學”,即回到人的生命本源性的創造,對人工技巧之能力有所貶斥。唐張彥遠論畫提出五等說:“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技巧之工整,落於下品之中。而影響深廣的逸神妙能四品論,更強化了張彥遠的觀點,據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的解說,四品之中,一種“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的逸格高立眾品之上,成為藝術創作的最高範式,這一範式,就是不遵法度的“拙”的精神。而淪為第四品的能品,雖有技巧的完善,但人工的成分濃厚,走的是技術主義的道路,是所謂得人工之巧,失天性之拙,所以受到貶抑。
在這其中,莊子的技進於道成為中國美學的重要創造原則。北宋末年鑑賞家董逌論李公麟的畫時說:“初不計其妍媸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耶。”[7] 又評李成繪畫說:“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8] 這裡所說的“不計其妍媸得失”、“忽乎忘四支形體”,都是對技的超越,而強調天機自放。在中國美學看來,藝術是心靈的遊戲,而不是技術,技術乃藝術創造之手段,但創作者不能成為技術的奴隸,動輒操規矩,舉繩墨,按形塗抹,傾心雕刻,計妍媸,較工拙,這樣便會現筆墨之痕,難掩破碎之相,成為技巧的奴隸,法度的奴隸,傳統的奴隸。中國美學強調“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不期於似而生意發之,遊戲於筆墨而法度忘之,無適而不往而窒礙破之,無心於巧而大巧得之,筆跡天放而不入畛域,持造化爐錘,秉天地神功,任其天放,隨物賦形,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
明董其昌等論南北宗,認為南宗以拙為法,北宗以巧為法,二者一走“化工”的道路,一走技術主義的“畫工”道路。清沈宗騫談到“化工”時說:“當夫運思落筆時,覺心手間有勃勃欲發之勢,便是機神初到之候,更能引機而導,愈引愈長,心花怒放,筆記態橫生,出我腕下,恍若天工。”③ 化工是無目的的,畫工則有目的;化工是妙悟的,畫工則沒有放棄人工和知識;化工優游不迫,畫工則傷於刻畫;化工可冥然物化於對象之中,畫工則是物我了不相類。他們又將工巧之類的藝術,加以“行家”的惡諡。將循拙法創作,稱為“利家”之作。如董其昌認為仇英的畫太用功,“刻畫謹細,為造物拘”,這種全憑工力的畫,被他歸入“習者之流”。董其昌的擁護者、清人李修易說:“北宗一舉手即有法律,稍覺疏忽,不免遺譏。故重南宗者,非輕北宗也,正畏其難耳。”[9] 沈宗騫還將重技巧之藝術稱為有“作家氣”,他說:“士夫與作家相去不可以道裡計。”所謂“作家”之“作”乃造作之作,是有為,是機巧。而他們所提倡的創作方式是“不作”,“不作”而任由自然,由智慧去創造,而不是由機巧去創作。
中國美學中這綿長的反技巧傳統,強化了美學中重體驗的思想,但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如在繪畫中,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蔚成風氣,高明者自臻高致,至其末流,則演變為胡亂塗鴉,以色貌色,以形寫形之風全然拋棄,不從工夫中進入,而等待著一味妙悟,阻礙了繪畫的正常發展。清笪重光《畫筌》指出:“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托士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製難成。” 所謂藏拙欺人的方式,的確是存在的。
| < 前一個 | 下一個 > |
|---|
- 2011-04-07 - 初唐四大家之首 - 褚遂良
- 2011-01-07 - 文徵明行書《明妃曲》
- 2010-12-20 - 葉朗: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 2010-08-10 - 如何理解老子的“道”,方爾加
- 2010-08-08 - 中國文化軟實力與文化安全- 王岳川
- 2010-04-19 - 歐陽中石:中華文化的核心是什麼?
- 2010-03-12 - “朱德群繪畫,陶瓷作品回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