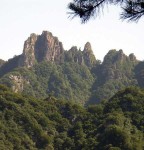| 文章索引 |
|---|
| 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國學大師的荒誕人生 |
| 第二頁--到底為何入獄? |
| 第三頁 |
| 第四頁 |
| 第五頁 |
| 第六頁 |
| 第七頁--我們失去了文化判斷力和敬畏嗎? |
| 所有頁面 |
三個疑點
這些年,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之後,文懷沙先生頻繁亮相於電視、報紙、網絡各種媒體,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
在各媒體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於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體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文革”經歷,係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斗”。
事實果真如此嗎?
1910年出生,還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2。約1953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併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與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88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於給早年經歷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文懷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與魯迅是前後弟子。
據查,1934年秋天,67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 1936年6月14日,病逝於蘇州。但在1963年文懷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於1921年,1936年才15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後,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麼關係,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見過?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1928年18歲的文懷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後任上海劇專教授”。按1921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7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於年齡提前了近12歲,抗戰期間的經歷也就容易豐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歲秋,於重慶作《聽雨》詩 :'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唸書,只有17歲,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誇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於天,於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於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文革”經歷,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於其入獄原因,一篇報導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於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後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處報導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與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對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1957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2009年2月10日與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姦污婦女十餘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後長期在天津茶淀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改。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文革“期間文懷沙並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於文懷沙在“文革”中的經歷,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於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異,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並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懷沙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懷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髮、消瘦的面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懷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後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麼,這一點卻被
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證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於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云:“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云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係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
我贊同徐先生的判斷。層累歷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李輝:我為什麼要質疑文懷沙?
自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報》刊發《李輝質疑文懷沙》(拙文原題為《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後,不少網民和記者都一再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麼現在要寫這篇文章?”人們想知道,我忽然發出質疑,是否因與文先生有個人糾葛所致,文在視頻談話中,也編造一套我曾在狗年採訪過他的說法,試圖將我的寫作動機暗示為人際恩怨所致。人們還想知道,我公開質疑,到底是想“一鳴驚人”,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因此,為使媒體同仁和公眾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必要將自己為何決定質疑文懷沙的歷史緣由、寫作動機和文化思考詳加敘述如下。
一,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關於文懷沙先生的行狀以及入獄原因,我不是因為突然間心血來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報》工作期間,就已經對此熟知,迄今已超過二十五年。
1982年初,我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晚報》,先是擔任文藝記者,後任副刊編輯。同年夏天,王戎先生從上海來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師賈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慶從事戲劇運動,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我在上海唸書時就與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風、路翎、牛漢等先生之後,他說:“我再帶你去看幾個戲劇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後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忙。”
< p> 我們先去看了鳳子、沙博理夫婦,然後去看望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時人們習慣簡稱為“青藝”)的導演石羽先生,張逸生、金淑之夫婦。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經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張、金夫婦早在抗戰時期就活躍於重慶話劇界,曾參加了郭沫若的話劇《屈原》的演出。從此,我與他們開始有了往來。來往最多的是張逸生金淑之夫婦,他們所住的青藝宿舍,在東單三條的一個不規則的四合院裡,離《北京晚報》很近,我成了他們家的常客,有段時間幾乎每週都去吃飯。院子裡住有好幾家,記得都是青藝的人員。我去的時候,常常能碰上他們在一起聊天。青藝是文懷沙工作過的地方,自1953年調入,到1963年底入獄,前後達十年。正是從青藝老人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文懷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隨後認識的蕭乾、文潔若夫婦,與牛漢先生一樣,都是文懷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從他們那裡,同樣聽到過關於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時我與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來,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懷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為研究巴金和撰寫《蕭乾傳》而去採訪卞先生的,後來,編輯“五色土”副刊時,又請他新開“居京瑣記”專欄寫稿。他寄來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銘》,是為他們的房子遇到麻煩而呼籲的。他們住在乾麵胡同中國社科院宿舍的頂樓,每遇下雨,房頂就往下漏水,夫婦倆不得不四處用臉盤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溫不火,改“陋室銘”為“漏室銘”,把窘狀描述出來,令人同情與焦慮。文章發表後,有了很大反響,我當即與房管部門聯繫,他們也馬上派人去樓頂重新鋪瀝青,從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為此事,卞先生專門來信致謝。也是因為這一緣故,我去他們家的次數也更多了,我們的通信也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與書信,我珍藏至今。
後來,從一些文學界的前輩那裡,知道青林很有才氣,寫過小說。自然,他們也談到過與文懷沙相關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諒他在她懷孕和坐月子期間做了某件事,才決定離婚……
;因此,可以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懷沙其人其事廣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聽。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經公開,使人有“爆料”之驚。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這些事情,大多避而遠之,當時的許多文化界活動中,也就很難見到他的身影,這一點,查閱當年的相關報導即可得知。
雖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從沒有想到要寫出來。第一,他不是我所關注的對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從來沒有把他視作一個文人;第二,在我看來,這屬於個人品行,是受害者與法制部門管的事,何況他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不過,雖然我沒有公開寫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響的範圍裡,卻盡量不讓媒體朋友報導他。幾年前,《南方都市報》記者來北京做一個文化老人系列採訪,請我幫忙聯繫周有光、楊憲益、王世襄、黃苗子、黃永玉等,名單上本來還有文懷沙,被我毫不猶豫地淘汰。吉林衛視有個《回家》文化紀實欄目,專門拍攝文化界名人與故鄉、母校的關係,從一開始我就擔任這個節目的藝術顧問和策劃,一次,製片人曾去聯繫過文懷沙,但我堅決反對:“這個系列裡,不能有他。”很高興,他們採納了我的意見。
這便是我二十多年來對文懷沙先生所採取的一貫態度。
二,十年來懷疑其真實年齡
開始懷疑文先生的真實年齡,是在最近十年,其間他的名頭越來越大、媒體曝光率越來越頻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形象,而儼然已成顯赫的公眾人物。對其真實年齡產生懷疑,主要源於多年來我與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藝家群體,最初形成於1943年抗戰期間的重慶,主要人員有唐瑜、吳祖光、呂恩夫婦;金山、張瑞芳夫婦;高集、高汾夫婦;戴浩、盛家倫、方菁、薩空了、沈求我等。經常來此的則有丁聰、黃苗子、郁風、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馮亦代等人。而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夏衍,被他們尊為主心骨。
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數,又相聚北京,開始幾年一些人就住在東單棲鳳樓的一個院子裡,是為“北京二流堂”。棲鳳樓往西,是青藝大院,往南又稱西觀音寺,與長安街相交,對面即是目前《北京晚報》所在地。
自八十年代以來,我與“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來往,寫過其中的黃苗子郁風的傳記,寫過丁聰、馮亦代、吳祖光、夏衍等人的畫傳或評論,還為有的人整理過日記和書信,對於他們的為人和歷史,應該說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近二十年來,這些老人經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還有楊憲益、王世襄、範用、華君武、姜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隨著一些老人的逐漸飄零,這一聚會的規模越來越小,但在2008年秋天黃苗子先生住院之前從未中斷。
據我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批判“二流堂”的小報專號,文懷沙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員之中,對他的介紹是“文化流氓、壞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獄”。文懷沙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確與“二流堂”有過來往,但並無過深關係。他們的回憶文章,或者閒談,從沒有正面提到過文懷沙,更不用說敘述彼此之間往來故事。相反,如在閒聊中談到此公,他們從來都是一種鄙視口氣。對於近十年來文懷沙忽然間聲名雀起,並被各種媒體冠以“大師”或者“風流”的稱謂,“二流堂”健在的老人們頗感意外和驚訝。他們感嘆時代變了,對人的評判標準也變了。但是,如果有什麼媒體將他們與之相提並論,他們還是會認為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譬如,前年,某電視台錄製一組文化老人節目,分別有文懷沙、黃苗子等,黃苗子獲知後,頗感無奈,不住地說:“真要命,怎麼把我和他擺在一起了? ”
不限於黃苗子,與“二流堂”關係密切的黃永玉,也對文懷沙持鄙視態度。 2006年春節,我所在的報紙的文化新聞版發表黃永玉所畫狗年生肖漫畫,同時還發表了文懷沙的迎新文章,並將兩者加框放在一起。黃先生的畫是我約來的,遂將報紙送去,他一看,只對我說了一句:“李輝,我該夸你還是罵你?你們怎麼把我和文懷沙放在一起了?”幾天后,文化新聞版的編輯告訴我,文懷沙看到報紙後,也說了一句話:“哦,黃永玉呀?我們是老朋友了。”
關於文先生的年齡,也是我與這些“二流堂”老人聚會時談到的話題。有幾位老人的出生年份為:唐瑜,1912年;黃苗子,1913;丁聰,1916年;郁風,1916年。屬牛的黃苗子先生今年96歲整。他們的疑問是:文懷沙本來比我們小,怎麼現在比我們大了呢?
不過,這一懷疑,大家都是飯桌上議論議論而已,並沒有想到要公之於眾。
三,兩年前決定追尋真相
我決定追尋文懷沙的真相,源於兩年前的一次刺激。 2007年,在郁風老人4月去世後不久,吉林衛視“回家”欄目的製片人李冬冬女士來看我。如前所述,她告訴我,她曾去找過文懷沙,想拍一個他的專題節目,當然我不贊成。談話中,她告訴我去見文的過程。她說,她介紹這個欄目曾經拍攝過黃苗子、丁聰、郁風等,文一聽,馬上就說:“哦,我和郁風是好朋友。幹校時候,她還找過我,為我畫裸體像呢!”
我一聽,脫口罵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訴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間郁風一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不可能去過乾校!文懷沙完全是胡說八道。”
我寫過郁風老人的傳記,總是以“老太太”稱呼她。郁風的父親郁華是民國大法官,叔叔鬱達夫是著名作家,他們兩位在抗戰期間先後被日本侵略者所殺害,是有名的民族豪傑。郁風正直,坦誠,甚至天真,她從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經歷炒作自己,在我們的聚會中,她永遠是一個中心,以率真和爽朗的笑感染大家,為大家帶來快樂。她的去世,令我們感到難過不已,沒有了她,聚會也從此少了熱鬧。
這樣一個讓我敬重與懷念的老人,這樣一個在“文革”期間真正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遭受七年磨難的老人,剛剛去世,卻讓一個因“詐騙、流氓罪”入獄、自稱也關押在秦城監獄的人,潑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靈一定不會安寧!對如此卑劣之人,我決不能原諒!決不能漠然視之!
這就是我決定要公開質疑的一個最直接原因。它關乎個人感情,也關乎對歷史的敬畏。同時,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讀者根據我的文字,只知道我是一個溫和、行文節制的人,他們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時也是一個倔強、固執甚至不給人留情面的人,周圍的同事和朋友,深知這一點。
四,今年元旦,決定公開質疑
兩年來沒有停止追尋,所蒐集到的史料和佐證,越來越證明文懷沙的自述與光環——年齡、入獄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諸多疑點,必須公開質疑,找到真相。 2009年元旦前後,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使我決定撰寫《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職的報紙,連續兩天刊登整版廣告,突出推廣“百歲國學大師文懷沙主編”之大型套書《四部文明》(每套售價數萬元),聲勢之大,讓人驚嘆。我和報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編輯部咖啡廳喝茶聊天,那幾日,我們談的是文懷沙其人其事:他的歷史陳跡,近年的聲名鵲起,特別是他如何已經被成功地“包裝“為“國學大師”。顯而易見,成為“國學大師”之後,他不僅自己四處題字、演講帶來經濟效益,隨著一套據說要取代《四庫全書》的一套書的推廣,將一方面牟取更大經濟利益。
《四部文明》的價值和歷史地位,不在我的評價之列。但是,由一個有歷史劣跡且又編造個人歷史的“國學大師”領銜主編,無法讓人接受。報社同仁鼓勵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尋與質疑盡快公佈於眾。他們說得好——不能讓文懷沙認為神州無人;不能讓世人認為媒體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讓後人笑話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標準和勇氣。
正是在他們的鼓勵與催促下,我在春節之後完成了這篇質疑文章,並請這些同仁分別從法律、史學、文字表述等方面幫忙把關。可以說,質疑文章雖係我個人所寫,但從另外角度說,它也是一批媒體人的情感與思考的集中體現。在此,我深深感激他們幫我完成了一個夙願。
五,我們失去了文化判斷力和敬畏嗎?
不到十年,文懷沙忽然間被媒體和社會製造成“國學大師”,足以令人們深思之。
中國曾經歷政治運動頻仍、“知識越多越反動”、“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時,陳寅恪、梁漱溟、陳垣、馮友蘭、錢鍾書、沈從文等堪稱文化大師的人依然健在,但我們顧不上珍惜和呵護,卻讓他們不斷地寫思想檢查,進而在放羊、種菜的勞動中消磨生命,這對於中國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實在是巨大的歷史遺憾。
隨著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變化和國力增強,人們對文化越來越熱愛,對文化人也越來越敬重,投資文化的興趣和實力也越來越大。隨之,對文化大師的出現,也越來越渴望。特別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希望藉弘揚“國學”而增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懷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國學大師”並以此獲取最大利益的可能與空間。
各界人士對文化老人特別是“國學大師”的尊敬、愛戴的情感,無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們輕信一個被稱作“國學大師”的招搖撞騙、欺世盜名也可以理解。問題是,我們的時代為何失去了文化判斷力?為何失去了對大師這一稱號的應有的敬畏?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向觀眾和讀者推介一個“國學大師”時,竟顯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碼的學術評判標準,就可以把“大師”的桂冠輕易地戴在一個人頭上,而不管對公眾和歷史的責任,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具有的文化敬畏。
質疑文懷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響,超出我的預料。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我們的公眾多麼需要歷史真相,多麼需要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師,多麼需要真正對得起後人的文化成果!
說實話,我最擔心的是,質疑文懷沙及其反響,僅僅成為媒體的一次狂歡,之後,誰都顧不上反省,又一切歸於原狀。不管怎樣,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發表新的意見。我將回到既有的寫作計劃中。更多真相的追尋,可以由有興趣的其他記者根據相關線索去完成。
2009年2月24日,於北京
| < 前一個 | 下一個 > |
|---|
- 2011-05-06 - 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悲秋題材與文人心態
- 2011-01-23 - 坦然面對死亡 - 大同歷史名人李少蘭
- 2010-10-09 - 光明日報:東西美學的邂逅——中美學者對話身體美學
- 2010-09-16 - 大自然之歌
- 2010-08-19 - 大歷史觀宗師 黃仁宇先生 詳細介紹
- 2010-02-14 - 老不糊塗:羽扇綸巾葉劍英不亂情場定乾坤
- 2009-12-12 - 成功靠天靠地靠自己(俞敏洪)
- 2009-06-25 - 綠壩係統提醒你,以下內容包含不良信息(韓寒)
- 2009-06-24 - 廖氏憤青教材(轉載)
- 2009-05-03 -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五四運動--(摘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