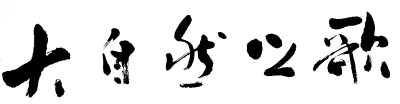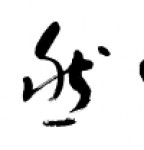陈世旭,著名作家。汉族。1948年生于南昌市。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将军镇》、《世纪神话》等多部,以及《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陈世旭卷》等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多部。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车》、《镇长之死》分获1979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首届鲁迅文学奖。
很久了,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水泥的森林、钢筋的湖泊和塑料的草原,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很久了,因为已经适应了人工的世界,人类的退化成为一件更为可悲的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大自然的存在,听不到流云的欢歌,看不到蓝天的舞蹈,闻不到大地的芳香,再没有福气享受生命的狂欢!
很久了,虚拟的电子网络复制着我们虚幻的快乐,真实离我们远去,真切离我们远去,真知亦会随之离我们远去吗?
为了寻回人生的真谛,让我们随同著名作家陈世旭,踏上这次回归大自然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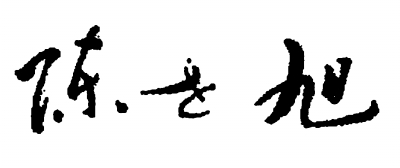
森林
在整个世界,除了水,我最喜欢的就是森林。
繁衍自强的森林是生之意趣。森林收容了一幕又一幕悲喜剧。
弥漫在森林间的沉寂与神秘,为艺术提供了深沉、宁静的心理背景。多少个世纪以来,森林始终滋润着人们的乡愁与诗心。这就是为什么索尔·贝娄会说:“艺术从森林开始。”
森林多么好。森林有花有草,森林有云有雾,森林有风有雨,森林有泉有湖……
森林有诗。
要摆脱无名的羁绊,我最想走向森林;要拯救疲惫的灵魂,我最想走向森林;要吟唱隐秘的心曲,我最想走向森林。
花与树的缠绵,云与雾的交融,风与雨的相伴,泉与湖的交响,无处不是诗的流淌。云聚云散是诗,花谢花开是诗,草飞草长是诗,月圆月缺是诗。森林是诗的宠儿。
走向森林,常常是我的梦想,我的渴望。
在森林任何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都会有风吹落潮湿的种子。季节更替,在森林到处荡漾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倾听森林的语言,你将成熟,聪明,坦荡,洞悉真理……生活的困惑与感伤随风而逝。走在森林,你会发现你是快乐的,森林是无声的呼唤,充实了你原本空洞的灵魂。
因为惰性和缺乏勇气,我任从自己常年被囚禁在嘈杂的城市。城市也是森林。楼群像树林,只是没有枝叶没有花朵没有果实,没有令人恋眷的狗尾巴草的清香。孩子们长大了,不会唱“采蘑菇的小姑娘”。楼群的颜色顽固,隐去了季节的界限;窗口在夜晚筛下星星,挤窄了无边际的想象;钢筋水泥傲然挺立,带来了坚硬工具的压抑。这是化工森林。在这里,躺着的心事结成青苔,站立的思想竞争阳光,人们掩起私下里表情丰富的脸庞,让善意和温情在陌生中蛰伏窥望。
只有森林才会有真正的歌唱。森林的歌,嘹亮、清逸而深远。森林里最多的是树,每棵树都是歌手。
走进森林,走进歌声,走进激动的曲调和流畅的节奏。带着幻变的梦境,灵感和鸟语花香,离开城市的喧嚣,演奏自己的乐章。让漫天的音乐的羽毛,化作无边的新绿与嫩黄。等待心灵的撞击,等待灵魂的再生。
我见识过世界的不只一处森林。每次我都会力图进入森林的深处。穿过茂密的、散发着浓郁的树脂和草莓香味的松树林,心里泛起一种甜丝丝的快感。林中的湖泊像美人的镜子,波光粼粼地闪烁在无边森林的怀抱,映照着蓝天的纤尘不染和青山的雄浑与妩媚。
那些树林是没有猎人也没有伐木者的。那里的鸟是不害怕被人惊扰的。头上树桠上,这儿那儿站着不知名的鸟。它们大大方方、满不在乎地站着。不时地懒洋洋地一跳。有时候落到离你很近的地方,然后又扑扑地飞起,它们拨起的风,直朝你脸上吹过来。柔顺的,毛茸茸的松鼠就在附近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蹲在离你最近的树枝上和灌木丛中,睁大眼睛滴溜溜地打量你。所有的生灵都充分享受着作为这片树林的天然主人的特权。
森林无疑有一种凝重的隐喻性质,暗示出生活最为深沉的一面。森林是生命的典范,告诉人们生命的原始法则。
潮湿的凉意从四面八方袭来。鸟悄悄地离开被太阳晒得温暖的树梢,振起翅膀,依恋地、默默地飞进树林深处。雾在林中飘荡。雾是半透明的。并不妨碍仰望树缝中的天空。被树枝分割的天空特别明亮。让我想起南方家乡闪烁的星光,被星光照亮的丰沛的河流、绿树中的城市和织锦般的田地。让我想起世上所有我经历过的美好事物。莱蒙托夫说得不错:“当我们远离尘世而跟大森林接近时,大家都不由得变成孩子了,心灵摆脱了种种负担,恢复了本来面目。”契诃夫是那般动情:“不可思议的大森林啊,你永远放射着光辉,美丽而又超然,你,我们把你称作母亲,你本身包括了生与死,既赋予生命,又主宰灭亡。”托尔斯泰则给森林赋予了道德意义:“置身于这令人神往的大森林之中,人心中难道能留得住敌对感情、复仇心理或者嗜杀同类的欲望吗?人心中的恶念应该在与作为美与善象征的大自然接触时消失。”当艺术家用圆舞曲为森林染上一片圣洁,“手风琴也打不破的宁静”的抒情节拍展现着快乐与忧伤,有多少人已经如梦如幻,走进博大与深邃。如果有一天,你坐在森林之外的地方,梦想曾经的家园,你便会知道,失去绿荫,灵魂就失去了庇护。混浊的噪声从耳边掠过,你将嫉妒并且哀怨,谁曾拥有过那片森林?
我多么愿意住在这样的树林:在森林幽静的小径徘徊,鼻翼里全是青涩的气味,看或枯或荣的草在夕阳下泛着柔柔的光,像长发飘逸;在绿叶沙沙的伴奏下唱歌,唱消失的爱情和不可知的未来,听或深或浅的水在林子的深处汨汨流动,像精灵呢喃。等有一天终于唱不出声音的时候,就安静面对树叶的私语。风拂过思绪拨动迷离的眼神。卷起的红松皮被阳光照耀,摘它一片,发现东风沉醉于此的秘密:暗香诱着彩蝶,在树木之间传递着甜蜜。绿肥红瘦都被遗忘,而你将保留森林中的这一缕暗香;等有一天终于不能呼吸的时候,就溶入树下的泥土,无声地悠悠地去到森林的漩涡深处,肃穆,庄严,神秘,而心,颤栗。然后在返青的季节,同蚂蚁、蚯蚓和飞虫、同所有卑微的生命一起,用柔软的头颅叩开泥土的门,迎接春天的来临。一声鸟鸣,心便永不寂寞。
草原
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的眉头像未解的结,你的脚步疲惫而蹒跚。
我把喧嚣的城市留在身后,我把拥挤的人群留在身后,我把所有的躁动和冲撞留在身后。
把自己交给苍茫。
你失落了什么?你要寻找什么?你想得到什么?
我问蓝天,我问大地,我问。
草原,向我张开博大的襟怀。从两边涌到路上来的、被露水淋得透湿的花枝和草棵子殷勤地拂着我的裤腿,像默默的爱抚。
古老而烂漫的草原。埋藏无数卜骨、陶片、断简、残碑的土地;站立长城、寺庙、黯淡的宫阁和拓荒者废墟的土地;横亘叱咤风云、如狼似虎的壮士演习杀戮的古御道的土地。
王朝的连营埋进深草;将军的鹿角没入沼泽。方尖碑如断锷。水泡子是饮恨苍天的眼睛。从刀光火石到金戈铁马,从血流飘杵到冠盖如云,皆杳然如苍狼呜咽。帝王的霸业连同古战场一起退出历史,一个鞍马部族的史诗在季节河道声息干裂。
而草原依旧。
高耸的大陆板块空旷恒大,弓起球面的脊线。草原把最广阔的空间留给七彩泛滥。芳草年年绿,碧色直铺天涯。千万种花如潮水,汹涌漫卷草原。乳汁洗出的天空,云舒云卷如峨峨高髻、荡荡裙裾。苍鹰盘旋,大道似瀑布。
真静啊。天地间是一片亘古的肃穆。远远的什么地方,好像有人在动情地唱歌。那是幻觉。只有风,只有白桦林,只有不甘寂寞的杜鹃、野百灵和蜜蜂在私语。
思想就像徘徊在迷离草莽的孤马,你会一再地想起那些似乎遥远的、已经忘却的过去,心里无端地涌起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却是幽深的甜蜜或忧伤。你会感到好像早就有过这种体验,要不就是做过一个和眼前的情景极为相似的梦。但是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一生中的哪个幸或不幸的时刻,你怎样也记不起来了。生活就像流水一样,淙淙地从你身边流过,你失落了很多,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
最远的地方,热浪蒸腾的高坡,号角悄然耸起。最初是一对,然后是一簇,然后是一片。然后,草原生命交响的高潮赫然君临。
万种天风骤然狂作。骏马雄壮的肌群,突起为跳跃的峰峦。马群纵姿跋扈,从远方或更远的远方潮涌而出。
大宛汗血天马从西极承灵威、涉流沙而来,从黄河负图而来。与犁铧一起耕耘生民的艰辛;与刀斧一起划破凝滞的血海;与香车一起装点贵胄的荣华。你为文明所依赖,你也为文明所驾驭;你为文明所恩宠,你也为文明所束缚。
什么时候,文明放逐了你,文明又解放了你!
于是你重又成为草原的王者至尊。自由与奔放重又成为你的特权。铺张扬厉的野性重又回到你的身上。天风滚滚,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啊,你重又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走云连风,吞吐大荒。
狂舞的铁蹄在我的血管里奔腾,惊心动魄的轰响是冰河破裂一泻千里。我忽然明白了我的沉重;我忽然知道了我的寻找;在地震般的颤栗和闪电般的快乐的瞬间,我忽然领悟了生命的开端和终结的全部欢乐和痛苦的奥秘:挣脱欲望的缰索,卸下诱惑的鞍辔,去呼应草原生命大气磅礴的抒情,一种另样的、博大的爱情——爱生活、爱生命、爱大地,直到永远!
夜要来了,多情的落日在吐力根河对岸向草原告别。暮色像紫丁香,有一个骑手在火红的天边向远方顶礼。
草原像人的心灵——当心灵纯净而充满幻想,它就变得无比深邃——深邃得能容纳整个世界。
我走在七月黄昏的草原,草原的路通向一切道路。远处是辽阔明亮的地平线,身后是觉醒的脚印。
这一天多么好!整个世界像在童话里变了样子。这样的日子一生也许只能遇见一次。这样的日子一生只要遇见一次。
感谢你,草原!感谢你金灿灿的光,蓝湛湛的水,甜丝丝的风和轰轰烈烈的生命。
在怒放的花丛中尽情留连吧,在熊熊的篝火前尽情跳跃吧,在生命的潮水里尽情徜徉吧。火在颤栗,酒在燃烧,舞在踢踏,灵魂在响着黄钟大吕的律动。当黎明再来,金子般的朝霞又会喷薄而出,我又将远行,让圣洁的大光明永照朝觐生命的虔诚。
湖泊
湖泊,上吞众水而下哺巨流,大气磅礴以波动日月。湖泊是“大地的眼睛”,看透了千年的沧桑。在湖泊操练的兵甲曾令天下四分五裂;在湖泊厮杀的豪强曾立江山于大一统;在湖泊汹涌的鲜血、浮沉的尸骨和萦绕不去的悲歌曾使历史瞠目结舌;在湖泊驻足和歌吟过的有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文章家。湖泊是云的故乡,水的故乡,生命的故乡,神话、英雄和诗歌的故乡。
湖上的无数岛屿,是乡土社会的史书库,漂浮在蓝天一样明亮和广阔的湖面,正是我常常莫名地向往的岛屿,拥有着美丽、成熟、淳朴以及大自然超常宠爱的岛屿。立于楼头,四面是粼粼发亮的茫茫湖水,点缀着鹭鸟翻飞的岛子和机船上冒出的袅袅轻烟;楼下,夹在老屋和新墙之间的幽深村巷里,响着当地盲艺人的古老弦子和渔鼓。如果说我曾在城市的生活中一度觉得亲切却陌生、虚荣但似乎不真实,那么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这里的人群陌生却亲切、也许缺少虚荣但真实可信。它远不止是地理意义上的梦境,还同时是文学意义上的梦境,它就存在于现实中,还将存在于无数人的想象中。
湖泊是我永远的精神故乡。我的青春——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是属于它的。我在湖泊播种希望,流了汗,还有血。生活,用巨大的、甚至是可怖的风暴和洪水,同时也用暖人的阳光和鼓动帆的风,粗暴而又温柔、无情而又宽厚地铸造了我的生命之舟。在那之后,我的关于欢乐与痛苦的最深切的经验,我的最热烈与最阴沉的情感,乃至我创作灵感的源泉、我的审美理想以及艺术追求的激情和情致,都是同它联系在一起的。
清晨,风在水上滑行,湖边的泊船轻轻地摇动,偶尔撞出亲昵的响声。一只水鸟在桅杆顶上打了个趔趄,翅膀散开来,拍了几下,终于站稳。然后就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不时勾下头,啄一啄羽毛。
大白天,天和水在很远的地方连接起来。天上一丝云也没有,水被天照出一片白亮,刺得眼睛生痛。不时有冒着浓烟的拖船拽着的驳船,和缀满了补丁的绛红色或土黄色的帆从那白亮上划过。
薄暮时分,最远的天边,横着条状的金色云霓。巨大浑圆的太阳在那条云霓上面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将要进入黑夜的世界。一行雁笔直地向上扬着,在它面前缓缓移过。一片帆长久地在太阳的圆心处停着,凝然不动。淡淡的紫色的暮霭弥漫过来,把湖罩在一片柔和明亮的光晕里。
到了夜晚,雾气一团一团在黑暗深处浮起,湖上的航标灯飘忽不定、时隐时现。然后,远处越来越清晰地现出一些起伏不定的轮廓,那是对岸的山峦。渐渐地,山峦上的光亮越来越广大,似乎有个人高挑着一盏雪亮的灯,正从容不迫地在山的那一面攀上来。那盏灯终于一点一点地从山脊露出,漫无边际地照亮了幽蓝的夜空。这是月亮。所有的星星都隐没了,而在默然里涌流的湖粼粼地闪起光来。湖边的蓼草静静地摆动,偶尔响起鱼跃的声音。几只水鸟被惊起,拍着翅膀从草尖上掠过,又消失在另一片草丛中间。
数也数不清的湖汊,汊汊有人家。到夜晚,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村落,纷纷亮起灯火,跟满天的星斗互相照应,让你明明白白地入了梦境,分不清是星斗落在了湖里,还是灯火点在了天上。
湖上诸岛,家家开门临水,村民淳朴,古风犹存。浮于荡荡碧水藏于森森古樟中的渔村,时有若雨若烟、似有或无的弦索之响,丝丝缕缕的水韵芳馨,令人疑在一个遥遥旧梦。
湖泊的一切生灵皆被视为神物。生灵有知,也把湖泊当作了天国。夏候鸟白鹭是湖泊的王者。白鹭飞时,两脚向后伸直,远远超过尾巴,两扇宽大的翅膀缓缓鼓动,从容不迫,气度非凡。白鹭是韵在骨子里的诗,是朴素和高洁的形象化。丽日之下有白鹭翩飞,蓝天便有了心跳的动静;细雨来时水田里站了一只两只白鹭,水田便成了一幅玻璃的画框;山岩上有白鹭群立,山岩便登时有了蓬勃的生气;夕阳里有成行白鹭低飞,更是乡间日子的一种恩惠。而冬候鸟白鹤则更其壮观。一个又一个从云端钻出的鹤群,长羽临风,翩跹而来;长喙含云,吟哦而来;长跖踏浪,高蹈而来。漫天是惊心动魄的鹤舞和鹤鸣。辽阔明亮的湖面,跃动着千姿百态的鹤影,仙子一样的尊贵,处女一样的纯洁,士大夫一样的优雅。
雾气在被云霞照得斑斓的湖面悠长悠长地漂浮。远山是一抹淡淡的烟痕。风吹着唿哨,在苇丛上掀起涟漪。隔年的枯草里,素净的白蒿、翠绿的筅帚菜、肥硕的铁扫帚、柔韧的马鞭草和纤细的碎米花一堆堆地汹涌绽放。生命萌动的气息四处弥漫。湖滩上的鹭或鹤,对人视若不见,或埋头在水里寻食,或专心啄羽毛,或昂首阔步高视徜徉。壮硕的水牛卧在草丛,与那些轻盈的鸟默契着,憨憨地眨着滚圆的眼睛。
哦——嗬嗬嗬嗬嗬嗬——
湖心有船起了呼号。船夫怡然,橹似摇非摇,手指指点点。
湖泊远离尘嚣,澄澈透明,在一个环境日渐使人忧虑的世界,或许是最后的一泓清水,最后的水上香格里拉。
百年前的哲学诗人已然预感到人类必将重返故里,重返童贞。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人的内心,永远存在着一个“故乡情结”。那是一种温暖的情感的凝聚,是无尽的梦幻和永久的魅惑。整个人生就是一次精神之旅,每一步都在寻找最终的故乡,所有朝圣者的疲惫,都会被故乡的烟火镀亮。
湖泊的光芒穿透了生命的意义,湖泊是精神生命的原点。湖泊是云、水、阳光孕育的骄子,而我愿是鱼,是鸟,是水柳,是爬满岛屿的白蒿、马鞭草和碎米花。我将为水的灵魂所吸引,依靠着帆在风云间行走,从路途到心灵,从喧闹到安静,张开双臂,去拥抱自然,去与乡亲交谈,去聆听最质朴也最灵动的语言,去享受最真实的美。是的,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那么我们何妨拓展生命的宽度。
河谷
峻峭的河岸上,星罗棋布的村寨缀满了海拔千米的山坡。山脊悬空的巨石,古碉和煨桑塔矗立,那是生殖崇拜的象征。整座村寨都处在它的威仪之下。触摸着它粗糙的肌肤,仿佛触摸一个久远的符号。神灵已经在雪山上生活了几十个世纪,一个民族原始的思维构架倚山而立,暗示着时间的悠远。它们是生命和美丽的保佑者,这是一种执著的坚守,守望灵魂永恒的驿站。
村寨的女人,花头帕,红长裙,古韵悠然,优雅端庄,一如从远古款款而来。风中飘动的鲜艳裙摆,如同对面绵延的山势此起彼伏。历史的流风遗韵与现实的千娇百媚交织成迷幻的梦境。
埋藏得太久的河谷,揭开羞涩的面纱,以娇艳的盛妆,捧出撩人的风情,给世界一个惊艳的姿势。寨子的烟囱袅袅炊烟升起,寺庙苏醒的法号低沉而悠远,不知名的万紫千红烂漫绽放,倾听背水女孩胸前清脆的铃铛。
深深的河谷,从昨日禁锢的古堡吹奏出世外的天音。
山脚下翻腾的河水,无声地咆哮,看上去平静异常,流淌在太阳、月亮、白云、雪山、土地、青稞、劳作、酒碗以及睡梦中,只有仔细谛听,才能得到时间深处的消息。河谷蛰伏于雪山深处,延续着古老的民俗,时间与空间神异结合,成为真正的世外桃源。叠翠的山峦,湍急的河流,黑色的碉楼,洁白的石屋,头帕与长袖,篝火与舞蹈,演绎着河谷儿女自在的日子。
那个傍晚最让我动容的是晚饭时见到的端茶壶的女孩。在那间色彩斑斓的木屋里,她带着幽谷的清香缓缓从客人身边走过,给所有人上过茶,便静静地把铜壶搁在窗台,然后倚窗而立。她的心一定在轻轻跳动,仿佛初恋的震颤从月色中传来,而情歌就在手上的铜壶里翻滚。
窗外,也寂静也灿烂也冷清也温暖,不知从哪里传来琴弦的拨动,弦韵为煮茶的暖烟滋润。女孩高高的鼻梁上的大大的眼睛迷离而潮湿,柔润的小手无端拂拭已经铮亮的铜壶,似乎在翻阅渐渐成长的情怀。轮回重复的安宁与恬淡的岁月,填满了希望的华年。一行行来自远古的歌谣,一阵阵行云流水般涌进鼓胀的心房。
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依然留在那条河谷,沉醉在最初的花香泛滥的黄昏。我希望自己每天傍晚都能够在那间斑斓的木屋里饮茶,看着那个端茶的女孩在窗边默默地伫立,像飘在云朵上的一个遥远的花的剪影。
我的文学观
读文艺史,我敬重的是那样一类艺术家,即他们创作的表达与他们的人格,与他们所表达出的价值观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好恶、爱憎是一致的。我喜欢的艺术家,他的人格是刚直不阿的,他的创作表达带有宏伟的气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但事实上也未必一定有言,作者的人格很高尚,作品就一定好?这也不一定。所以,不如这样说吧,如果人格很高尚,作品成就也很大,这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也是我最敬仰的。
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我认为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给一代人、给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至高的思想视野,把我们整个眼界和心胸展开到一个非常广阔的程度;另一方面,艺术表达有开创性,艺术家的思想能力所达到的高度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达到的。他的表达给后世的艺术家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伟大的纪念碑式的人物的产生决不是随意的,而是时代和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但我们可以崇尚他们,景仰他们,努力去接近他们,使自己的工作变得有意义。
艺术家应该是“静”的。就是那种“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的“静”;那种“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的“静”。“静”是一种境界,能不能“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家的命运。伟大的作家首先是有“静心”的作家,他是生活的思考者,生活的评判者,当然也是生活的参与者。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变化的世界而没有“静心”,那就只能随波逐流。“静”是指内心的“静”,内心没有躁动,没有过分的欲望,唯一所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静静地思考,静静地表达。整天躁动不安、费尽心机不拿这奖那奖誓不罢休的艺术家,其作品到底有多少艺术含量是一件很可怀疑的事。
一个艺术家整天忙于给自己涂脂抹粉,搔首弄姿,肯定是徒劳。真正的艺术家,为艺术生,为艺术死,不会屑于在媒体上保持自己的新闻性,让自己成为一个明星。恰恰相反,他会努力避开世俗的纷繁。真正的好作品,可能一时得不到重视,但最终不会被忽视。沉得住气,就会有好作品,大作品,大艺术家。
| < Prev | Next > |
|---|
- 2011-05-15 - The New York Times: Is Truth True? Or Beauty? A Couple of Thinkers Go Deep
- 2011-05-08 - 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从清末新政失败说起
- 2011-05-06 -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悲秋题材与文人心态
- 2011-01-23 - 坦然面对死亡 - 大同历史名人李少兰
- 2010-10-09 - 光明日报:东西美学的邂逅——中美学者对话身体美学
- 2010-08-19 - Great Master of Macro History, Mr. Ray Huang
- 2010-04-05 - 文怀沙现身武汉 自嘲:我是什么大师?狗屁!
- 2010-04-05 - 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
- 2010-02-14 - 老不糊涂:羽扇纶巾叶剑英不乱情场定乾坤
- 2009-12-12 - 成功靠天靠地靠自己(俞敏洪)